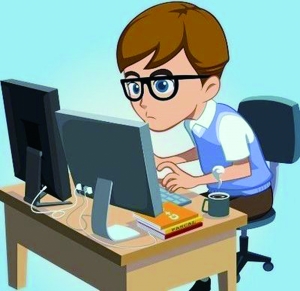这个秋天有点落寞,树上叶子往下洒落,都是懒洋洋的,一片一片飘在空中,半天也不着地。
老爸退休了,说是说谁都有这一天,而一旦面对,就像婴儿断奶一样,开始总有些不适应。
早七点准时醒,七点半习惯地提着包去上班。到点了,发现一向准时的车未到,拍拍脑门这才想起,已经不要上班了,自我解嘲,哑然失笑。
有人看中了他的才华,请他在一个文学团体任职。但他一生淡泊清静惯了,感觉难以适应那种喧哗,婉言谢绝。
退休了,该享受了。一些老友找上门来。“打牌去,喝茶去?”知道那时间会容易打发,他似乎找不到感觉。打牌一辈子没学会,喝茶么,他性子急,从来就是牛饮“一口干”,不习惯一点点大的杯子慢慢品。“钓鱼去?好有味啊!”“好是好,那我坐不住。”“摄影很有趣,高雅!”“我恐怕做不来。”“旅游啊,遍览风光,乐在其中!”“我喜欢静,到处飘有什么好的。”
找上门的一拨一拨,三寸不烂之舌都无法将他劝动,无尽的诱惑而他却心如止水。说多了,反而惹他烦了。刀枪不入,水火不浸。 找上门的没辙了,渐渐地一个个不敢再自讨没趣,纷纷敬而远之。
守在家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他怔怔地坐着,一坐就是半天,可怕的安静。老伴有意安排他去买菜,但往往是碎了鸡蛋,倒了豆腐,失了钱包,狼狈得不敢进门,就像说了谎话的小孩被大人识破那样的不好意思。那做点家务吧,洗过的碗总是粘乎乎的,拖过的地板总是水渍渍的,炒菜要么咸得涩口,要么忘记放盐。没有一件事做得好,越帮越忙,令人哭笑不得,只好让他“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生活习惯的改变,带来性格的变化。一向温和的他,动不动就爱发脾气,而且孤僻、固执,才退下来不到一个年头,苍老却明显加快了步伐。
退下来,见过不适应的,没见过如此不适应的。这样下去,家人都担心他的身体心理健康。
人活着,不能“坐吃等死”,总得有点事做,有所寄托。日子不能这样过。
母亲忧心忡忡地找儿子商量。
儿子在机关任中层干部,写得一手好文章,在圈内小有名气,当然与父亲的熏陶很有关系。
只不过是父子俩之前谁也不买谁的账。父亲的文章古板、严谨、细致,儿子的文章飘逸、散漫、粗放。为此,他们经常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
在承担单位的公文写作的同时,儿子还从事文学创作,尤其是散文、随笔什么的,常常忙得焦头烂额,自顾不暇。
父亲赋闲,好的文字功夫却白白派不上用场。
电光火石之间,儿子忽然想到,完全可以把这活儿推给老爸,老人家坐得住,耐得烦,认真细致、投入,不二人选,而且感觉会很好。
晚上,儿子推脱了一切应酬,陪着父亲喝开了。几杯酒下肚,老人家兴奋起来,平时惜话如金,今天说个不停。趁势而入,儿子顺竿子爬,说我最佩服父亲的文笔,我无论如何努力都赶不上,还要请老人家手把手教,不吝赐教。诚心诚恳,掏心掏肺。从来不苟言笑的父亲此时脸上却笑开了花:“看你这油嘴滑舌!”此事显然是达成默契了。父子俩那晚把一瓶酒干了个底朝天。
多年的文字浸淫,儿子功底也不浅,但是送父亲的校稿、改稿常常破绽百出,标点符号一顿乱打,错别字随处可见,而且用典也不讲究,远远不是以前的风格,明显的漏洞百出。
为儿子校稿、改稿成了父亲的功课,有空就坐在书房里,戴着老花镜,逐字逐句不放过一个疑点,常常有时改得面目全非,而且附上长长的批语。
每天下班回来,父亲会把校正的稿、改过的稿拿来,一一点评。儿子呢,正襟危坐,像学生听课般认真,而且头点得像鸡啄米。
“你呀,不是我说你,说过多少遍了,一篇文章怎么逗号逗到底?明不明白标点符号的作用?”父亲说。“是我不注意,养成了习惯。”儿子赶忙认错。
“瞬间的‘瞬’,你总是少了个‘目’的偏旁。错别字打堆,数了一下,一篇千字散文,错别字竟然有几个,你出洋相啊!”父亲指责。“我的基础太差了,真不应该。”儿子接着检讨。
“用典,不要堆砌。你提到古人读书,一口气用了‘李密牛角挂书,囊萤映雪,范仲淹断齑划粥’等十几个典故,是不是在故意卖弄?”父亲不客气地批评。“是的,是的,有些故弄玄虚,弄巧成拙了。”儿子一个劲地解释。
常常是父亲说,儿子听。但有些时候为了不同看法,父子都得理不饶人,吵得一塌糊涂,谁也不让谁,是母亲出面调解才罢休。
这日子从此过得热闹起来。父亲的书房里摊满了各种资料,一待就是半天,经常感到时间不够用。
父亲乐此不疲,渐渐地身板硬朗起来,性格也恢复到从前。生气、活力弥漫房间,笑容经常挂在脸上。
殊不知,文章中的许多错误、漏洞是儿子有意制造的,存心要让父亲去发现去纠正,在发现中在纠正中父亲才能寻找到快乐。
有活干的日子不会冷清,充实的时光不会落寞。
文章中的许多错误、漏洞是儿子有意制造的,存心要让父亲去发现去纠正,在发现中在纠正中父亲才能寻找到快乐。且看——
心语杂谈
心语杂谈
扫一扫,新功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