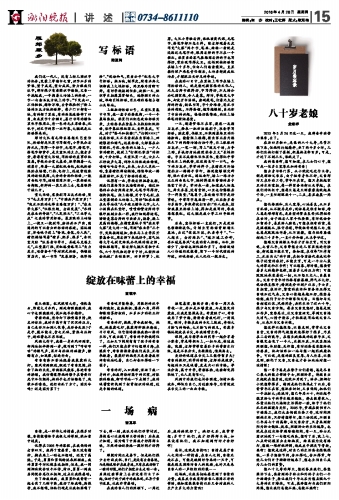那时大队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标语都是队员书写制作。小学民办老师元久,写得一手好字,毛笔字、排笔字、粉笔字都拿手,是文宣队的主力。能者多劳,每每有重大活动,写标语的差事非他莫属。学校办公室大桌面,经常搁着一大碗墨汁,堆着一大摞红纸白纸。红纸标语张贴在墙壁、门柱、电杆上,迅速营造浓烈的运动氛围。大会的会标和标语,一般用白纸书写。运动源源不断,一茬标语泛白撕毁,新鲜的一茬又粘上去,笔墨难得干枯几日。
重大活动,需要刷写石灰水标语,留下“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人定胜天”、“工业学大庆”之类的常用标语。最显眼的土砖墙上,一拨又一拨刷写,涂抹并不严实,隐隐约约可以看出旧标语的痕迹。因地制宜,谷仓垛子刷上“备战、备荒、为人民”,猪栏矮墙写着“猪多、肥多、粮多”,会议室内贴“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正堂屋门柱,用红漆黄漆写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对联式标语。供销社商店内,统一书写“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说话和气,买卖公平”红色大字号标语。挑石块,刨草皮,所有水库大坝都嵌上大幅标语,两里路外清晰可辨。有时学校接到任务,放假一天,组织学生担箢箕背锄头,选择醒目的山坡,堆砌巨幅标语,用正确的思想占领山头阵地。
上级拟好标语口号,文宣队员集中书写,熬一盆子面粉浆糊,一个一个屋场张贴。社员们以红色政治标语为荣,主动要求在阶基木立柱贴红纸标语,似乎象征根红苗正、吉祥喜庆。可是,对于“要斗私批修!”、“打倒×××!”这类标语,又不乐意刷在自家墙上,回避影射和晦气。这类标语,大都落在公家猪栏、牛栏、仓库的土墙上。一户人家的猪栏,被刷上“打倒孔家店”的标语,十分打眼。文宣队员一走,女主人不好放声大骂,刮除又怕犯政治错误,嘀嘀咕咕老半天。后来,女主人灵机一动,靠着猪栏那堵矮墙,悄悄堆放一排高粱秸秆,不见了标语的痕迹。
记得有一次,学校老师挑着灰桶,到我们屋场写石灰墙壁标语。读过私塾的公办老师周老师,毛笔字写得好,领衔执笔。爬上楼梯,用中号毛刷,在正堂屋侧面土砖墙上,写好“把农业摆在头等地位”九个端正楷体大字。大人小孩围在禾堂坪,啧啧称赞老师的字像印版刻出来一样。我仔细观摩运笔,暗暗羡慕老师的书法功力。接着,换上更高的楼梯,在横堂屋垛子写“农业学大寨”更大的一幅。写到“农业学”三个字,突然接到通知,要求马上去学区开紧急会议。周老师下来洗好手,客气地将大号毛刷交给民办代课的陈老师,请他继续写。陈老师大概只有初中文化,六十年代初过苦日子时,从衡阳冶金机械厂自动离职,回乡种萝卜、红薯。大队小学缺老师,派他顶岗代课,毛笔字、粉笔字都不怎么样。陈老师硬着头皮写完“大寨”两个字,笔画、结构一看就是没练过毛笔字的,跟周老师的字不在一个档次。社员当面客气恭维陈老师的字也写得好,背后说写得太丑。这幅联袂标语留在墙上十多年,任由人们恣意褒贬。直至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土砖房拆建成红砖房,才摆脱品头评足的命运。
在我的心目中,在黑板上写字在墙上写标语的人,就是能吃国家粮的文化人。元久老师书教得好,字写得好,不久转公办吃国家粮,令人羡慕。那时,学校发大字本,却没开书法课。磨砚提笔,仿着元久老师的神态,胡乱书写,字十分难看,毫无书法的韵致。不得要领,越写越糟糕,自此断了书法的兴趣。偏偏好高骛远,向往上墙举笔的潇洒感觉。
一天,趁着爹娘不在家,浸泡一灰桶石灰水,捡来一把旧油漆刷子,准备学写标语。脸皮薄,怕献丑,不敢到屋场里的外墙涂鸦。偷偷架上楼梯,将自家正房内楼枕木下的两排砖墙打扫干净,沾上浓浓的石灰水,一笔一划,写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长幅标语。字虽不成楷体宋体黑体,觉得比平常作业本上的规整,欣欣然长吁一口气。余下的石灰水,学爹的样子,在猪栏内外墙壁粘出一排排手掌印,据说能够驱灾辟邪,保六畜兴旺。满地白印,墙上一路方方正正的白色大字,映衬得原本昏暗的房子亮堂了许多。爹回来一看,知道我人细鬼大,舞文弄墨,没有责怪,心里也仿佛像房子一样亮堂:“鬼崽子,喜欢读书写字是好事哦。平常写字鬼画符一样,以后要多看书多练字,争取考试打百分!”外人进来,惊讶我屋里标语上墙,得知是我写的,夸我思想最红。这大概是我小学三四年级的事。
后来,宣传标语一直流行,只是政治色彩渐渐淡化。计划生育标语曾经铺天盖地,出过“该流不流,扒房牵牛”、“一人超生,全村结扎”、“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之类的雷人标语。而今,标语少了,话语也理性温和多了。标语鼓动人心传递行政能量,留下一个时代演进的印迹。回味标语,让人记住一段历史。
陆亚利
雁郊原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