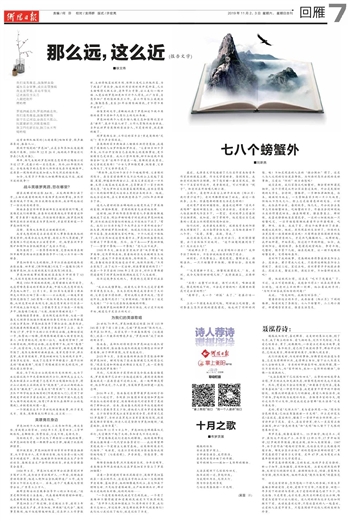我们怀揣美好,而美好的事物,仿佛曾经的浪漫与青春,总是来得那样炽热,走得那么匆忙,留下让人焦虑又让人企盼的生活。古老的时钟滴答作响,轻抚耳膜,像一位不老的老人,而“窗外树木,犹如一支阴郁的蜡烛”,仿佛一位固执的人。
“大海在堤坝下已经低吟四天”,往事的回味能带来安慰,岁月的流失却充满焦虑,好像明亮的时光也不能抚平。然而,有爱就不会让你绝望,“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是一种意外惊喜,我更看重平常中的平静的愉悦。就像此诗的最后几行的描述,看爱人面容温存,放下诗书,拿起针线为我缝补内衣。在物质丰富的今天,缝补之术尽可以失传,但是我还是企望那“低头温存”之美不要失传。
是的,有爱“无须点灯”。美与爱会照亮一切,“因为你金色的秀发/已向这角落投射一片光明”。什么是妙笔生花?这就是。最后两行,驱散了一首诗中的全部阴郁,让一首诗开出了花来。爱人,在这首诗里,诗人一直没有正面去描写,却以“金色的秀发”和“光明”给人留下了无限的想象和空白。
布罗茨基,俄裔美籍诗人。15岁辍学,做过车工、司炉、医院太平间运尸工、水手等13种工作,17岁开始写诗,32岁被剥夺国籍,驱逐出境,后加入美国国籍。1987年,由于其作品“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文学上及敏感问题方面,都充分显示出他广阔的思想和浓郁的诗意”,布罗茨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年47岁,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布罗茨基诗歌风格,总的来说,他的声音是安静的。醉心于细节、具体描写、名词和发现。注重处理熟悉的事物,处理它们的微妙关系。语调倾向冷淡,词语、意象陌生而坚固,超然而客观。他的作品是“超然与客观”的最佳范例。
读完这首诗后,忽然想起一个诗人的告诫:不要太多篇幅去解读爱情。是的,爱情不可言传,只能意会。回想一年多写下的读诗与荐诗,关于爱情的诗篇已读下不少,仍无后悔。不是有意,也非无意,既然名利都是过往云烟,唯有爱与爱情可以让人铭记,这人间的诗与远方无论如何撇不下爱。我读我喜欢之诗,只想让喜欢的人一起喜欢,让爱的人在爱中重生,只想在阅读中记住人间的美好与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