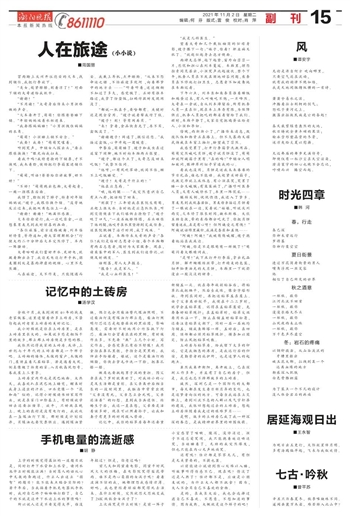■汤学汉
金秋十月,我来到阔别40年的战友老家做客。这里遗留着许多土砖房,不禁勾起我对老家土砖房的美好记忆。
我小时候就是住在土砖房里,是在土砖房里长大的。如果说乡愁是相隔千里的故乡,那么那土砖房便是乡愁的根。
我依然记得我家的土砖房。或许,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土砖房都是一个样子吧。土砖砌的墙体,木做的窗户,木做的门,屋顶盖着几层稻草。若是遇着大风,倒真像极了杜甫的家: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土砖房室内外也是泥巴地面。大热天,我喜欢趴在泥巴地上睡觉,醒来时我身上浸岀的汗水、口水竟像一个“花和尚”似的。记得小时候读书回家写作业,就是在家门口阶基上,有时候放学回去还要扯猪草、放牛,只好改在晚上。晚上的农村是没有电灯的,我就伏在一盏煤油灯下写。那时候是计划经济,买煤油也要凭票供应。遇到煤油紧缺,偶尔也会用柴油替代煤油照明。不过柴油灯没有煤油灯那么亮,柴油灯照明灯芯还总是起磨菇状的黑球团,影响亮度,需要时不时地用小竹签挑下灯芯。柴油灯会冒着浓浓的黑烟,有时候作业多,不免要“熬”上几个小时。写完作业,会感觉鼻孔有些不舒服!我用食指在鼻孔里抠,手指全是黑黑的。我伸出手给娘看,娘说:这个是柴油灯的烟脂,你快去拿毛巾洗一下脸,把鼻孔擦一擦。
嫩肩也要挑起男子汉的重担。因父亲在我7岁时就离世了,对我幼小的心灵及生活都是重创。在父亲离世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脑海中常常岀现“父亲没有死,父亲怎么会死呢,父亲还活着”的幻想。直到我当兵退伍、结婚生子后,我还一直在想,父亲要是活着该多好,现在可以照看孙子,让我和妻子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劳动。
记忆中,我住的稻草房每年还要重新铺盖一次。就在每年收割稻谷后,将稻草扎成把晒干,然后垒成垛,像金字塔形状。待到农闲时,再把这稻草盖在屋上。由于父亲离世较早,我便在十二三岁时,就学会盖稻草屋。记得在盖稻草屋前,先要备好稻草绳扦;在盖稻草时,稻草尖端要用水沾一下,防止在铺盖时稻草松蓬,还要注意稻草尖朝下,同时一层一层地均匀铺盖,铺成鱼鳞塔一样。盖好后,在四周、顶部都必须用稻草绳扦、横条加以固定,防止风把稻草吹散。
土砖房与稻草房,给我留下太多的印记。它是我栖息的港湾,是我远行后的归宿,是勤劳者的庇护所,也是追梦人的起跑点。
虽然我离开衡阳,离开故土,已在深圳工作多年,并且有了自己的房子。但是,我总也忘不掉那故乡的土砖房。
诚然,深圳已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每天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也是追梦者向往的地方。可每当我站在立交桥上,看到川流不息的人群以及气宇轩昂的建筑,我依旧想起过去的土砖房,想起土砖房伴随着我走过的艰难岁月……
是啊,故乡的土砖房已成了我一种深深的眷恋,是我精神世界里的田园牧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