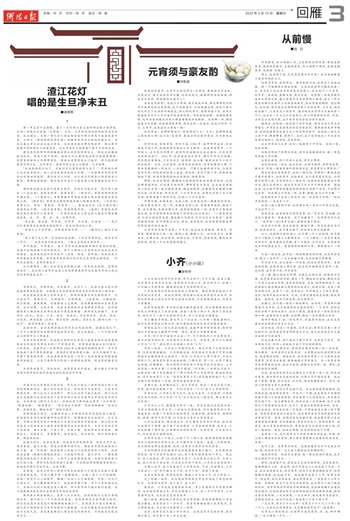■曾利华
小齐是西山村开中巴车的,年不过四十,个子不高,浓眉小眼。也许因为长年开车久坐,身骨架不大的小齐,肚子却不小,就像一个怀胎八月的孕妇,圆溜溜的肚子显得特别突兀。
小齐住的西山村和我住的东山村毗邻,都在距离县城四十多公里的山旮旯里。虽说是邻村,村民彼此间也熟得能叫出名字,但西山村和东山村并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而是相隔两座山,约有五六里路程。
这些年政策好,县乡的公路如蛛网般密布,穷山僻壤的西山村和东山村都通上了水泥公路。原在广东务工的小齐,便弃了货运生意,回乡买了一辆十五座的中巴车,专门往返城乡跑客运。
为了赚更多的钱,每天早上7点左右,小齐便一路按着喇叭,把中巴车开到我们东山村,提示要进城的村民快点到路边搭车。
村里就我们一家人住在马路边,我每年春节回家探亲,刺耳的喇叭声常把我从睡梦中吵醒。因而,我对小齐颇有微词。
当然,对小齐不满的不止我一个,不少村民对小齐也有意见,但不是因为喇叭声,而是因为小齐的小气。背地里,有不少人都称小齐为“小气”,甚至有人当面喊小齐为“小气”。
听我二叔讲,小齐这几年跑中巴车,确实方便了山里的老百姓,大家也很感谢他。小齐跑客运后,村民再也不用跑十多里山路到通乡公路旁搭车上县城了。然而,小齐这个人有个特点:不近人情特小气,谁想在车票上减他的钱,门都没有。有一次,山里下着毛毛细雨,冷飕飕的。西山村有个村民坐小齐的中巴车去镇上,上车后想减一块钱车费,小齐瞪着小眼说:“对不起,一分钱也不能少,如果没钱,请下车走路好了!”那个村民听小齐这样说,脸通红通红的,忍不住回骂了一句:“湾里就算你小气!真是越有钱越小气!”然后极不情愿掏出一元钱,悻悻地塞进投币箱。
自那以后,大家都知道了,坐小齐的车,钱是一分也不能少的,否则,很可能会被赶下车。不知不觉中,“小气”成了小齐的绰号。
尽管如此,小齐本人并不生气,也从不在乎。小齐觉得,只要你付足乘车的钱,叫小齐或“小气”又不伤自己一根毫毛,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小齐为人小气,驾驶技术却不一般。毕竟是跑过长途货车的,尽管山里的路又窄又弯,一些地方还很险峻,但车技娴熟的小齐,驾起车来,就像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沉着冷静,该快时快,该慢时慢,减速、转弯十分平稳,从不会让人在车上晃来晃去。
小齐也很爱车,每天跑完车,自己都亲自用井水冲洗,把车内打扫得干干净净。脏了破了的座椅套,小齐会及时更换。在车上,小齐还配备了塑料袋,以供晕车的村民使用。大家觉得,小齐虽然小气,但坐他的车挺舒适的。
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山里下了一场小雪,纷纷扬扬的雪花飘在东山村和西山村的上空,天气骤然冷了起来。凌晨一点的时候,东山村的老李突发脑梗,其时,老李家只有老伴刘氏在家。
不知所措的刘氏披着外衣哭喊着挨家挨户敲门。大家聚到老李家后,有人拿出手机拨打120,有人帮忙掐老李的人中穴。慌乱中,我二叔提议,等120怕是来不及了,不如找西山村小齐。又有人说,找小齐是个好主意,只是这么冷的下雪天,小齐未必会同意吧?
七嘴八舌中,我二叔拨通了小齐的电话。可是,电话那头,小齐只是说了一句“黑灯瞎火又下雪,出不了车”,便挂了电话。
大家失望至极,骂骂咧咧的,都说小齐不仅小气,还不讲良心。
过了约摸一刻钟,东山村漆黑的夜空中突然响起了熟悉的喇叭声。大家异口同声:来了来了,是小齐!
看得出,小齐也是急匆匆赶来的,身上穿着的是冬季居家棉衣。大家把老李抬上车,刘氏也跟着上了车。在一片叮咛声中,小齐驾着中巴车,消失在茫茫的雪夜中……
据二叔说,那天晚上虽然大雪没有封路,但驾技超群的小齐沿着山路走,还是惊出了一声冷汗。好在老李被送到人民医院后,马上得到救治,才从鬼门关捡回了一条命。
至今,老李家还欠着小齐万余元。这钱显然不是租车费,因为那天晚上,租车费小齐一分也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