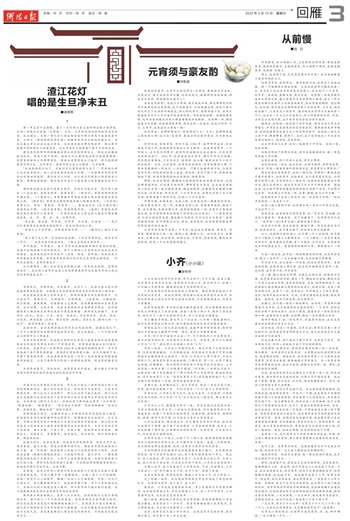■凌拥军
1
有一年正月十五傍晚,看了一天灯的人在土边和田边烧个稻草包,点响一封爆竹正在送“大年把”。突然,几声惊天动地的响铳声远远传来,远远望去,又有一堂几百人组成的由龙灯带头的花灯浩浩荡荡而来。山呐子(锁呐类的民间乐器)和铜号的声音尖锐地划破长空,似是从春天里又似是从远古传来,夹杂着大鼓大锣的鸣金声,衡山爆竹的爆炸声和耍灯人的嘻笑声,让元宵喜乐气氛弥漫了整个乡村和天空。
建自清代乾隆年间的塘坳湾堂土砖堂屋的神台上,两支大红蜡烛红闪红闪,照亮了整个堂间,抬起头可以看清楚海碗口粗的屋檐树、巴掌宽的弦木以及鳞鳞青瓦。两扇古老厚重的大门敞开,排灯进到神堂前作揖行礼,往外望去,堂前坪里已是人头攒动,人声鼎沸。
“水波堂的花灯来了,是我们自己屋里的花灯来了。”负责接灯的人认识这堂花灯,他一边向屋场里的住户介绍,一边和屋场里的长辈们讨论着如何接待,要打发多少灯钱。而小孩子们则在人堆里探出小脑袋,看那戏旗招招,看刀马旦手里十八般兵器以及各路各色戏中人物。
那时候老渣江区的灯类很多很多,多到记不起名字。花灯里人物如《八仙过海》里有吕洞宾、张果老等;《西游记》里有唐僧师徒和牛魔王等;《三国演义》里有曹操吕布周瑜刘备孔明关张赵黄马等五虎上将;《杨家将》里有佘太君和穆桂英杨六郎杨宗保等;《水浒传》里有宋江、李逵、鲁智深、燕青等……;甚至地方戏《毛不精打铁》里面的毛不精,《朱买臣卖柴》里面的朱买臣,《盘洞》里面宝庆府相公杨子荣和仆人安童等……只要社戏戏台上有过的人物花灯都会展演出来,生、旦、净、末、丑,应有尽有。
“推豆腐,磨豆浆,炸豆腐,四甲角,水豆腐,水泱泱……”花灯灯队里张果老在做推豆腐的样子,边走边唱边逗小孩;
“东姑子上了我甲船,去年想你到今年……”《桂阳江》艄公子戏东姑;
“堂上领了夫人命,去为相公送衣襟,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并作一步行......”这是安童为相公送衣,一路上走的是文丑戏步……
岁月悠悠,千年渣江。我十多岁住在独板桥新铺子屋场的时候,老渣江区域仅剩下的四堂花灯,除了三湖田心王家的花灯没来过我们的祖堂,凌新屋的花灯和刘氏坪(卫星、新屋、渔坪组)刘家的花灯年年都来拜年贺春,年年离开的时候打排灯的总是用衡山调唱道:“今年是没耍到,是明年再来补……”
灯火阑珊处,那一句扯得长长的衡山调“今年是没耍到,是明年再来补”,是我幼小童年对未来人生美好憧憬和对当时春节年味以及元宵佳节的意犹未尽……
2
为赏花灯,寻根年味,辛丑春节,正月十三,我前往渣江花灯源地凌新屋和水波堂,正好赶上水波堂的画师在为出灯的戏中人物化妆。
水波堂祖堂有两三百年历史了,依然保持着当年完好的样子。它古老庄严,雄伟大气。天间敞开,光线明亮。三进宽阔,六横纵深,柱子粗圆,梁栋檐挻。花板雕刻工艺精细,花鸟像塑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大厅四围,古色古香。化妆台由两张四方马蹄桌子拼成。画师根据戏里人物在给生旦净末丑各个角色画脸谱。画师彩笔轻描下,生分须生(老生)、红生、小生、武生、娃娃生;旦分青衣旦、花旦、武旦、刀马旦;净分花脸(正净)、架子花脸(副净);丑分文丑(衡阳人称“三哇子”,搞笑的角色)武丑等。
我很惊奇,这些农村堂客们并非专业化妆画师,轻描淡写之下,一个个人物惟妙惟肖瞬间就能画得出来,穿上戏袍后,一个个便如舞台上的剧中人一样逼真。
百思不得其解时,水波堂以前的灯队负责人凌鱼水和水波堂屋场发出去的凌台风带我来到一个老者家里。老者端出团盒让我们挂红,三杯茶后,老者拿出一本厚厚的1953年上缴国家税赋的本子,本子背后画满了各个角色的脸谱。原来花灯里的所有人物,是代代相传下来,早有了固有的形象,水波堂的画师也是一代代一直承传着这种精湛的画风和技艺,以至于每年花灯队伍一出场便成佳唱,深受赞叹备受欢迎。
辛丑年的春节,阳光灿烂,油菜花在风中荡漾,渣江镇上不时传来耍灯的开场乐鼓声和接灯的礼花在空中炸响。
3
中国古代元宵闹花灯的习俗,今天也只能从一些评书演义和小说里找得蛛丝马迹。渣江花灯由来已久,但时间已无法考究,只是至今保存完好。有人认为上古就有了,有人认为源于渣江春社,有人认为自大宋起衡州大地就传来了东京开封以及北方城市元宵同庆佳节的习俗。文天祥的《衡州上元记》,详细记录了衡阳城元宵节“士女倾城”“观者如堵”“骈肩累足”“咫尺音吐不相辨”的热闹场面和“百戏之舞,击鼓吹笛,斓斑而前”的张灯盛况。
传统的渣江花灯,主要由当地三大姓族王氏刘氏凌氏族人组成。其他姓氏在清代和民国年间也有花灯,但都被时光大浪淘沙,今已无存。今渣江耍花灯的户姓都是迁自黄河流域或中原地区。渣江花灯的内容是以社戏戏台人物表演和赞唱为主而流传至今。无灾无患的正月十五夜里,渣江古镇,六街三市,大街小巷,包括周边乡村屋场,都有社火,热闹非凡。笙簧聒耳,鼓乐喧天,花灯排街,观灯者和耍灯者,都密麻如蚁。
就渣江花灯,我访过长者,知道清代和民国年间:时值正月十五,西乡要塞,渣江古镇,周边乡村繁多的灯队,都会井然有序地涌向三街六巷,在“见风硝”的石板街上和板门门店里来回串门拜年。此时县丞官署(现渣江镇镇政府址)门前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一般能聚得境内各大姓十几堂花灯,三四千人前来排街表演,而观灯者更是不知几倍人数。那时与民同乐的渣江官署,只正规接待规模浩荡的花灯,其他龙灯狮灯多如牛毛,应接不暇。
长者说,凌家当时有三堂花灯和其他姓共十几堂花灯在渣江官署门前排街表演,只见人群中有一高强猛汉,头戴一顶十八斤的铜帽,身挂一副百斤以上的铠甲,脚踏一双四十八斤的铁鞋,手提一口九十斤的大刀,在人群里健步如飞。他走到官署门前,用个人身体挡住大门,其他灯队的人休想先进入署内,所以年年的灯魁非他们莫属。这个高强猛汉就是现水波堂很多年前的老前辈。
离开渣江回家的路上,我有一点点担忧。在对传统灯文化不重视的今天,耍灯的人一个个在渐渐变老,虽然有新生代在作薪火承传,但无论是花灯还是龙灯规模都越来越小了,还有很多灯类已经绝迹。渣江花灯栩栩如生几百年如故的人物脸谱,以及它散发出来的深厚的地方文化气息,在远离农耕进入商业信息化的今天,不知道它还能流传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