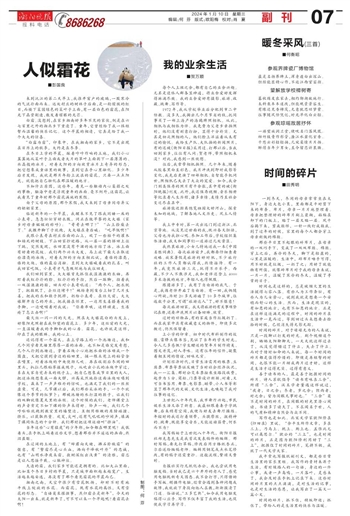■贺万顺
每个人上班之余,都有自己的业余兴趣。尤其是退休人群各显神通,将业余爱好发挥得淋漓尽致。我的业余爱好有摄影、旅游、收藏、跳舞、写作等。
1972年,我从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市二中任教。没多久,我掏出几个月节省的钱,托同事买了一部上海产的海鸥牌照相机。从此,相机与我相依为伴。我免费为父老乡亲拍照时,他们没有刻意打扮,显得十分朴实。尤其是初次照相的人,他们脸上洋溢着从未有过的愉悦。我给生产队、大队拍的新闻照片,有的还被《衡阳日报》采用过。打那以后,当我回到家乡,往往有人问:贺老师,带照相机来没?对此,我感到一丝欣慰。
往后,我常带相机拍照。几十年来,随着从胶卷黑白至彩色、底片冲洗到即时成影等变化,我先后更换了四部相机。自智能手机问世,照相机已失去了大众的宠爱。如今,我分门别类保存的照片有千余张,其中有的被《衡阳晚报》刊发。此外,我还保存视频、音乐相册等纪录着人生历程,诸多亲情、友情乃至社会变迁尽在其中。
旅游能近距离饱览祖国大好河山,探索未知的地域,了解各地人文历史、风土人情等。
我上中专时,第一次出远门到过浙江、北京等地。从没见过世面的我,既兴奋又胆怯,父母也为我担心呢。参加工作后,学校组织集体活动,我又和同事们一道游过几处景区。
我热衷旅游,小女儿特地送我一本《中国名胜词典》。每次旅游前夕,我都要仔细查看攻略。放寒暑假是旅游的好时机,不少旅行社的工作人员都认得我,热情接待。有一年,我竟然旅游三次,玩得不亦乐乎。西藏,不少人不敢涉足,我和老伴还登上4000多米海拔的地方,年轻人也得佩服。
跟团游多了,我有了自由游的底气。于是,我携老伴开启了自由游。有一回,我俩随心所欲,历时20多天游遍了10多个城市,往返数千公里,可谓“旅游达人”了,好不惬意!
每次旅游回家,我又将旅游的有关事项登记在册,还要冲洗照片以备回眸、欣赏。
过时的旧物品,有的家庭当作垃圾扔了。而在我家中具有收藏意义的物件,即使多次搬迁,仍然保留着。
上小学的印章、初中时代布料制作的校徽、雷锋头像书签,见证了当年的学生时光,令人几多感慨!学生赠送的贺年片制作精美、图文并茂,耐人寻味。还有往年的信件,凝聚着相互间的情谊,回味无穷。
计划经济时代,日常生活需用的粮票、豆腐票、布票等票证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状况,我一一汇集。那时公交车票按乘坐路段收费,起步为5分。商标、门票等设计新颖、耐看,又可当书签用。舞票、电影票、磁带、小人书等彰显了那年代的文娱、文化生活,也唤起了我对往事的追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市舞厅兴起,市民娱乐生活又添了新意。我最初跟着妻子学跳舞,后来稍有空闲,我便与好友去舞厅操练。年轻时的我还打着领带,头摸摩丝,挺精神的。跳舞,既能享受音乐,又能运动筋骨,何乐而不为?
我写稿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衡阳日报社郑克惠先生是我首次发表稿件的编辑。那时写稿,要先打草稿,修改后用方格纸誊正,尔后送给编稿老师。编辑用钢笔或点水笔修改,有的稿子还需重抄。这般流程,繁琐又费时。
自报社实行无纸化办公,我也尝试用电脑发稿。当时我已是六十开外的老人了,感觉用电脑既新奇又困惑。我不会打字,只得借助手写板。刚操作电脑,经常会遇到各种问题或故障,我就放下身段向他人求教,渐渐摸清了门道。俗话说,“工多艺熟”,如今我用电脑发稿得心应手。写作不仅丰富了我的生活,也促使我学习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