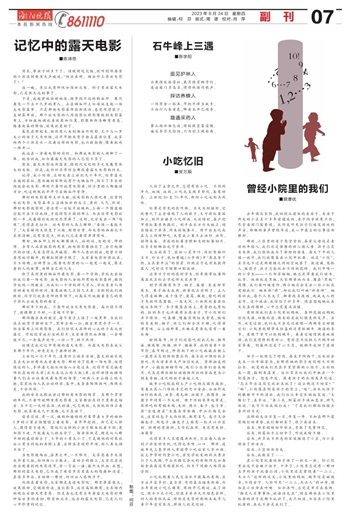■陈诗悠
周末,带孩子回乡下了。傍晚刚吃完饭,就听到邻居家的小孩在村巷里大声喊道:“快出来哟,晒谷坪上要放电影了!”
这一喊,竟让我有种恍如隔世之感。村子里放露天电影,已是很久远的事了。
于是,我赶紧收拾好碗筷,踱步到不远的晒谷坪。果然看见一个五十几岁的男人,正在晒谷坪上忙碌地支起一块大电影幕布。只是那块电影幕布很新很白,感觉用得很少。支好幕布后,那个放电影的人用投影仪将影像投到电影幕布上,并细致地调试着效果和位置,影像渐渐清晰有质感。随着夜幕的降临,效果就更好了。
暮色浓郁起来,陆续有人来到晒谷坪观影。几个七八岁大小的孩子尤为积极,还早早搬来凳子抢占最佳位置。我家的两个小孩是头一次看这样的电影,也兴致勃勃,像看把戏一样开心。
我站在一旁看电影的同时,和那放电影的人闲聊了一阵。他告诉我,如今看露天电影的人已经不多了。
想来,露天电影逐渐落寞,跟现代文化的多元发展有很大的关联。但是,我仍旧非常怀念那段看露天电影的时光。
记得,我小时候,正好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经常喜欢去姨妈家玩,因为姨妈家附近有个大晒谷坪,隔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放电影。那时只要听说有电影看,村子里的人都激动万分,吃过晚饭就早早守在晒谷坪等待。
那时的电影幕布又旧又脏,放电影的人很吃香,经常到处放电影,电影幕布上沾满俗世的灰尘、质朴、人气、热闹。那时电影投影时,旁边有一台胶片放映机,上面一个圆盘镂空胶片在不停地转,才能将影片投到布上。而且经常电影放到一半,或最精彩处就突然黑屏了。这时,大家发出一阵“呜喔”,觉得甚是扫兴。放电影的人马上解释:“要换一卷胶片了。”大家瞬间又恢复了兴致,期待非常。而电影的画面也不是很清晰,还有雪花点,但我们总是看得津津有味。
那时,晒谷坪上到处都围满人,站的站,坐的坐,蹲的蹲。当有人站在投影的光里,把电影影像挡住了,会引起强烈的公愤,大家急得大声喊骂。那个人意识到后,赶紧不好意思地闪躲开,脸都红到脖子根了。大家看电影时很认真,目不转睛,全神贯注,跟着电影里的人一起哭一起笑,像是看别人的故事,演绎自己的人生。
除了在村里的晒谷坪看电影,每一个学期,学校也会组织我们看一场电影。放电影的人会把所有的电影器材,搬到学校的一间教室。而我们一个学校好几百人,学校负责人便排好看电影的时间,某某班级几点到几点看。当轮到我们班级时,同学们就在老师的带领下,兴高采烈地搬着自己的凳子排队去放电影的教室。
那时年少的我,只要听说当天有电影看,高兴得不得了,连课都上不好,一直魂不守舍。
那间腾出来的教室,每个窗子上挂了一块黑布。当我们进去把凳子摆好坐下,黑布全部一拉,教室里黑乎乎一片。但当幕布上闪现影像,我们惊慌又澎湃的心也终于在此刻落定。学校经常放打仗的影片,大家看得热血沸腾。一会唏嘘不已,一会高声欢呼,一惊一乍,好不热闹。
这便是我记忆中有趣的露天电影。而露天电影在我父辈那个年代,却更是处于巅峰时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最大的娱乐就是去大公社看戏或者看电影。那时为了能看一场电影,住得很远的人,手举着火把从四面八方赶过来。记得作家范诚老师就在他的文章《流失在远山的火把》里,这样动情地描写着人们去公社看戏看电影的场景:“四面八方山路上的火把,零星地向人民公社移动、集中,夹杂着阵阵狗叫、阵阵欢笑,十分热闹。”
我的母亲也跟我讲过那时看电影的场景。在那个贫苦的年代,只要听说哪里有电影看,大家都会在村子里奔走相告。当干完一天的农活,洗好澡,吃完晚饭,大伙就结伴去看电影,就算要走几十里路,也不在话下。
母亲还说,有一次,姨妈和姨妈的对象带着8岁的她和5岁的小舅去隔壁镇上看电影,虽早早赶到,却已是人挤人,围得密不透风。像他们这样的小孩子根本就看不到,更加挤不进,只能看大人的后背了。母亲很机灵,硬是从人群中爬到最前面去了。5岁的小舅太小了,于是姨妈的对象就让小舅坐到他的肩膀上看,这样真是视野开阔,别人再也挡不住了。
当电影散场后,漆黑之中,一片哗然。大家亮着手电筒或举着火把,向四面八方散去。在回去的路上,大家还在谈论当晚看到的电影情节,你一言我一语,激烈又热血。我想,那时的露天电影,已然成了艰苦岁月里最大的慰藉和消遣。在很多年后,当回眸一瞥时,仍旧让人感慨万千。
而现在看电影,大家都是走进电影院。那里屏幕很大,效果很好,空调很舒适,座位很多,远近高低都有,坐在场内的观众安静又有素养。但是再也没有当年看露天电影时那种俗世里的亲切、野蛮和欢乐,远去的露天电影,已是人们心中珍贵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