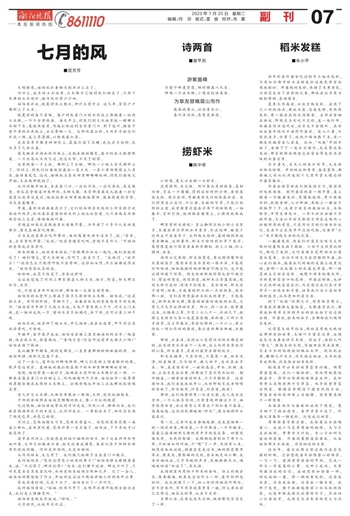■屈芳芳
天刚擦亮,姑伯就扛着锄头到河洲上去了。
河洲上,成片的玉米地里,玉米棒子已被村民们掰走了,只剩下焦黄的玉米秸秆,被河风吹得沙沙响。
姑伯告诉我,秋夏村水土肥沃,种什么有什么。这几年,家家户户都种上了玉米。
秋夏村的各个屋场,每户村民屋门口的水泥地上都摊着一地的玉米棒,一个个金黄饱满。每天早上,村民们到玉米地里把一颗颗玉米掰下来,装进麻袋里,用拖拉机运到自家屋门口。剥了包叶,摊在平整干净的水泥地上,让它暴晒一天。太阳快落山时,又用铲子把它们铲成一堆,盖上厚薄膜,以防夜露打湿。
走在杂草齐腰身的田坎上,晨露打湿了衣裙,我也是不恼的,反而多了几分欢喜。
霞光映在洋湖凼的河面上,泛起熹微的曙色,渡口的机工船静默着。一只水鸟从头顶飞过,划过天际,不见了踪影。
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种上了庄稼,哪怕一小块土旮旯都种上了。河洲上,村民们忙着收割最后一茬玉米。一条小黄狗跟随主人身后,摇动着尾巴。远处,插秧机正在水田里嘟嘟嘟地响,村民们抢收完早稻,又在抢种晚稻了。
从河洲散步回来,坐在屋门口,一边吹河风,一边吃香瓜,真是惬意。香瓜是堂嫂凌四英种的,又甜又脆。本家邻居屈反元挑着一担空箢箕从我身边走过,他说他要去田里挑秧板莳田,高高瘦瘦的背影,消失在晨曦里。
早晨,最热闹的要数燕子了,它们时而停在电线杆上伸长脖子欢快地叫两声,时而落在屋檐的晾衣杆上向远处张望。几只母鸡在对面的空地上觅食,咯咯咯地叫着。
堂嫂凌四英还在厨房里忙着做早餐。今年请了十多个人来田里帮忙,每天在她家吃两顿。
正当我进屋要去吃早餐时,姑伯驾着电动车过来了,说:“芳芳,走,去家里吃早餐。”我说:“就在堂嫂家吃吧,堂嫂不是外人。”可姑伯执意要我去家里吃。
回来的路上,姑伯母告诉我:“你跟那些妇女一起吃,她们会把你吃了!她们嘴尖,冒几句好话,你听了,会受不了。”我纳闷 :“说什么?”“说你怎么只晓得呷饭不会莳田。这些妇女呀,什么话都说得出来。”姑伯母很认真地说。
哈哈哈,我忍不住笑了,原来这样呀。
这让我想起了河洲上那长势喜人的玉米,粗犷,野蛮,却又那么朴实,自然。
哎,可惜没亲耳听她们讲,那场面一定很生动有趣。
姑伯家的禾堂坪上堆满了很多已剥好的玉米棒。姑伯说:“这是粘玉米,用作饲料的,等晒干了,准备卖给戈祠堂屋场养牛的戈晓阳。”姑伯家今年种了几块玉米地,玉米产量有两三千斤。对方上门来收,是一块四毛钱一斤。留四五百斤给鸡吃,余下的,还可以卖三四千块。
姑伯还说,他家种了糯玉米,早已摘好,放在冰箱里,中午用它来炖排骨吃,可香呢。
午睡中,窗外雷声滚滚。姑伯母在楼上屋里喊姑伯的名字:“杨喜桂,快去收玉米,要落雨哒。”“着吗子急?你没听说雷声大雨点小吗?”姑伯在楼下搭话。
我从睡梦中醒来,跑到走廊边,一直等着那场酣畅淋漓的雨。如姑伯所讲,雨终究没落下来。
过了一会儿,窗外依旧蝉鸣阵阵,蝉儿们在树上唱着颤抖的歌,歌声悠远深长。装秧板的拖拉机在楼下的水田里嘟嘟嘟地冒烟。
傍晚,姑伯拿着一把铲子,把晒在禾堂坪的玉米棒铲成一堆。一群麻雀落在屋门口的树尖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姑伯扯开一张厚厚的薄膜袋铺在成堆的玉米棒上。公鸡母鸡也开始三五成群地钻进鸡笼里。
老人铲完玉米棒,从裤袋里摸出一根烟,点燃,欣然地抽起来。
夕阳的余辉照在姑伯黑黝黝的脸上,像一片红的晚霞。
吃过晚饭,姑伯母说带我到河洲走走。河风沁凉,拂面而来。我们踩在铺满碎瓦片的乡道上,往河洲走去。一季稻出禾了,田坎边长满了狗尾巴草,颜色已转深。
河洲上,芝麻地随处可见,芝麻长势喜人。白色的芝麻花像一朵朵小嗽叭,在风里吹着。芝麻秆有一米多高了。姑伯说,下个月就可以收芝麻了。
漫步在河洲上,你能感受到稻子抽穗的劲头。知了还在热呀热呀地叫着,太阳已经躲进云层,把天边染成橘色,鸟雀们在夕阳的余辉里尽情地闹腾。河洲是热闹的,又是安静的。
从河洲回来,天已黑了。我们搬几把椅子坐在屋门口歇凉。
我问姑伯母:“您还记得您小时候的事不?”姑伯母瞪大眼睛看着我,说:“不记得了,哪还记得?”而后,我们都不说话。蝉也不叫了,只听见夏虫在黑夜里沉吟,水田里的青蛙偶尔附和几声。过了一会儿,姑伯母好像想起了什么,开始对我滔滔不绝地讲她儿时的陈年往事。
等我再看时间,已是十点了。姑伯母打了一声呵欠。
我对姑伯母说:“姑姑,时间不早了。我明早还要早起到古渡边走走,我们先上楼睡觉吧。”
姑伯母意犹未尽地说:“好吧。”
七月的风,从我耳边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