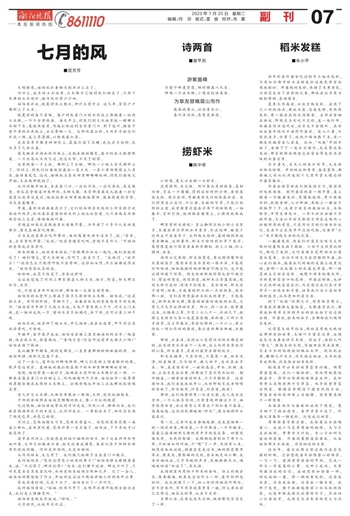■朱小平
幼年时在外婆家吃过的手工稻米发糕,不及如今都市糕点店的发糕这般色泽雪白质地膨松。外婆做的发糕,保持了米黄原色,兴许是包含了亲情的元素,那味道似乎更为暄软绵甜,余韵留长。
夏季天然高温,正适宜做发糕。浸泡了几小时的粘米,磨成米浆,迅速发酵,蒸熟的发糕,有一股浓浓的米酒醇香。左邻右舍相互转送,即便是当天吃不完的,盖一块纱布,收藏在阴凉通风处,次日也不会馊坏。在安放我童年的水乡渔村外婆家,进入小暑,日长农活多,忙累了,就找个理由歇下来,蒸一锅发糕犒劳家人亲友。比如,“双抢”早稻丰收了,母猪下了一窝壮实猪仔,或是有远客来访,那家的厨房烟囱总会冒出带发糕米香味的白雾信号。
水乡暑天,是大人的农忙时节,又是涨水防汛时期。年幼的我和哥哥,每逢暑假,都要被父母从垸内送到十几里外靠大堤边的外婆家躲水。
外婆会掐算好我们到来的日子,提前蒸好发糕迎候。到外婆家的第一顿早餐,桌上摆着一竹甑屉发糕,有圆鼓鼓的,有方块棱形的,软糯香甜,入口即融,再配上一碟坛子剁椒萝卜干,或者寸段长的酸坛豇豆,五味除苦,开胃生津爽口。一字不识且话语不多的外婆,无法以华丽文雅的言辞表达她内心酝酿封存的爱意,只是用朴实的行动告诉我们:生活不止是简单平淡地吃饭,还要有“点心”来点缀起生活的仪式感。
一甑屉发糕,使我们对漫长乏味又炎热难耐的暑假充满了期盼。小孩子生性贪玩好吃,刚吃了发糕,又吵着要去荒野湖沟打莲蓬采菱角。水性不好又不会撑船的外婆,担心我们溺水,拖着我们到她的菜园土地里巡视,看哪一丛瓜藤上的瓜最先蒂落,哪一畦芝麻豆子渐近老熟。她像个神奇的魔术师,不断更新零食口味花样。外婆这样做,也许不是纯粹地宠爱我们,而是想让我们在日常中多一些快乐和守望,培养我们自小感知幸福的能力,从而更加热爱生活。
到了“双抢”的那几日,邻里联手帮工,外婆在家操持大桌饭菜,无暇看管我们,便将我和哥哥安排到外公的挑谷担子后边拾谷穗。外婆说,捡来的谷子,全都给我们做新米发糕。
记得夏天的早稻谷,熟时没有秋天晚稻谷那样金灿深黄,禾梗叶片皆是浅黄,谷穗尾巴还夹着些许芥末绿。割谷子,渔村人叫“撩尖”,留很长的禾蔸,犁翻田后用来沤肥。参差不齐的稻穗挑回晒谷禾坪,脱粒机去屑,曝晒几个日头,风车扬去秕谷,生米就能煮成熟饭,就能做出稻香发糕。
稻穗在外公肩担的箩筐里抖擞,偶有滑落遗漏,我们一路拾捡,很快将收获把握在手。待外公倒掉稻穗堆在禾坪,我和哥哥立马爬进两个空箩筐,双手抓紧箩筐边绳索,眼睛在草帽沿下搜索风的方向,箩筐在曲折的田埂上边摇摆,感觉像荡秋千一样有趣。
禾苗在雨水与露珠的滋润下稳蔸,夏日晒干了稻谷进仓,离开学季不远了,外婆又准备蒸一锅发糕,打发我们回家。
哥哥抢着学推石磨,我抢着舀米添喂磨心。我说小勺是哥哥拾的稻穗,大勺才是我拾的,哥哥并不计较,专心于如何匀速运转磨盘。外婆端着脸盆在磨底,从容接住那点点滴滴、涓涓细流的米浆。
这些年,每当我因企望过高而迷茫无措的时候,总会想起童年添喂磨心的场景,一勺一勺,遵循哥哥推磨的节拍,完成一件又一件容易的小事。这种小成功,又重新激活我的自信,启动思维如推磨一样,顺反旋转一圈,将一锅稻香发糕,还原成米浆,还原成谷穗,还原成一株禾苗。我终于发觉,勤于拾掇起眼前小如米粒的收获,也能串联成微光流萤的日子,然后细心打磨品赏,也便是生活本身的意义与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