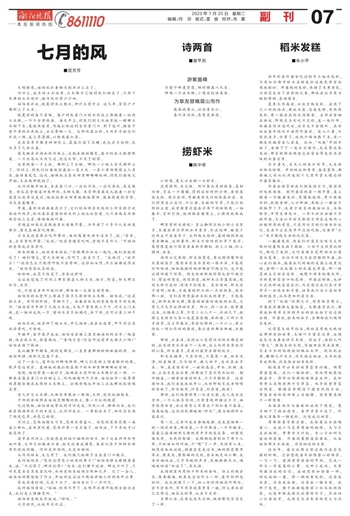■陈中奇
小时候,夏天必去捞一次虾米。
没有捞网,自己做。用竹条或茶树枝条,柔韧性好,弯成一个圆圈,得到这些材料方便,房前屋后大把。难点在网,有破鱼网或旧蚊帐最合适。我们村里没江没河,不打渔,没破网可寻,只能打蚊帐的主意。我曾偷剪过塞在凉席下的蚊帐角。一切备齐,穿针引线,把网缠在圈架上,小捞网就做成了。
哪里有虾米捞呢?靠山脚阴凉的小圳小沟里多,长着丝草浮萍的水井里多,水流喧哗、敞亮少遮的主干溪渠里少。太阳越大越好,最好晒到泥地烫赤脚板,这样暑热,虾米才纷纷到水草下乘凉,聚得像夏夜灯影里密集的长脚蚊。拎上小桶,抄上捞网,出发。
动作必定要轻。虾米很警觉,要让捞网像伸进水里的筷子,像原本长在水里的一根水草,不能有任何响动,细细微微的响动都会吓跑它们。也不能让捞网投下阴影,陌生的新鲜的阴影也会吓跑它们。得选好角度,悄悄推进,把虾米往角落里拢,赶到无隙可逃时,慢慢平抄起来。在水里时,虾米近乎透明,细看,才能看到虾头的一点深颜色,离水那一刻,它们在网里露出米粒大的身子,弓起尾来,拼命乱蹦乱弹,像暴雨砸檐时溅起的水花,总有几只又幸运弹回水里。所以,网一出水,赶紧覆过来,往桶面上罩,不管三七二十一,抖动几下,把捞上来的杂七杂八先震落进桶,再捡拣。小圳小沟多游草,边上有柴禾,常挂住捞网,一不小心,要么阻住一网打尽时的推进,要么连网都弄撕破,弄散架。
那时,水真清,清到让人觉得河沟的水都是甜的。我家村里水库底下一丘田,边上水圳里有冰凉的沁泉,虾米最多,是我们最常去捞的地方。
虾米在桶里,不显形的,只薄薄一层,回家洗净,倒在锅里,匀匀铺开,微火烘干,反而显出多来。虾,真是很奇妙,一碰到高温,开水、热锅、滚油,立马变色成金黄,好像涂了显形药水似的。揭开锅盖,一锅黄澄澄的虾米,只只弓腰驼背。此前捞回来,我们活泼泼地开心,此时即刻变成香喷喷的食欲了,虾米抵肉,炒韭菜,炒蒜苗,极佳!
那时,我们隔壁村有一位老大娘,没儿没女没老伴,一个人孤零零的,日常靠赶种猪过日子,她背驼得厉害,永远像背上黑罩衣下倒扣着只畚箕,高高坟起。远近村民都喊她“虾米”,因为她捞虾米最在行。
有一次,父亲叫我去请她赶猪。我走进她唯一的一间泥砖屋,那间屋,一半作厨房,一半作睡房,屋梁上挂满烟熏火燎的黑乎乎的炭灰条,四壁泥墙乌黑,光线好昏暗。我模糊地看到灶下有个人影,不知该如何叫她,只“喂”了一声。见到有人来,她慢吞吞地站起,颠颠歪歪走过来,她的脸色像黑罩衣,像炭灰,像昏暗的光线,原来她是双小脚。我告诉她地址,几乎用喊的声音,见她微微点头,喃喃地回道“知道了”,再无话。
我闻到屋内有烘干虾米的香味,但立刻跑出来,像要躲避、脱离或害怕什么一样,屋外却阳光灿烂。我也犹豫了一下,担心仓促间她没听明白,会不会爽约,用不用再进屋重复一遍,但父亲此前已交待过,她答应的事,从来不变卦。
自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她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