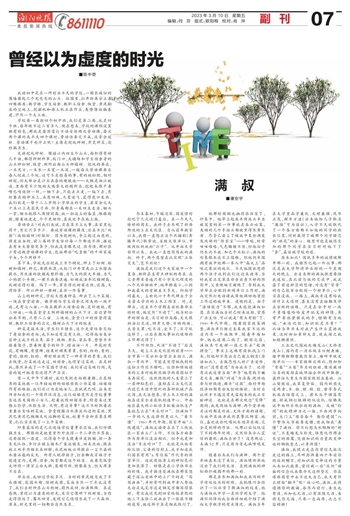■陈中奇
我读初中是在一所创办不久的学校,一圈长城似的围墙圈起几个光秃秃的山头。校园里,拉开距离分立着四栋楼房:教学楼、学生宿舍、教职工宿舍、饭堂。黄泥翻滚的空地上,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作业,轰隆隆地搞基建,俨然一个大工地。
学校第一届招四个初中班,我们是第二届,也是四个班,每年级不过二百多人。现在想来,学校的课程设置颇有特色,那就是每周雷打不动安排两次劳动课,每次两个课时或半天四个课时,劳动任务完不成,还常会延时。劳动课干些什么呢?主要是挖坑种树,开荒种菜,迎检搞卫生。
先讲挖坑种树。围墙以内四五个山头,面积得有好几千亩,都得种树种草,校门口、大操场和学生宿舍旁的山头种松树,饭堂、厕所后面山头种橘树。挖坑的要求,一米见方,一米长一米宽一米深,一般每次劳动课要求每人挖成三个坑。这可不是轻易的事,有的地松肥,相对好挖,但大部分是沙石混杂的硬坡地——大概是湘江故道,里面有不少饭碗大鸡蛋大的鹅卵石,挖起来跟干着嘴巴啃烧饼一样,一锄下去,只能去点皮,一镐下去,有时錾在鹅卵石上,石屑四溅,火星迸飞,震得虎口发麻。我们就是一帮十二三岁刚小学毕业的学生,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农民子弟,但身高都在一米四五左右,锄头一拿,锄头把跟人肩膀同高,挑一担运土的畚箕,踉踉跄跄,擦着地皮走,个子更矮的,箕底近乎在地上拖。
劳动苦么?对我们来说,实在算不上大事,在家里也得干,肯定只多不少。要说劳动课的强度,还真不比“双抢”(收稻插田)时轻松。因为挖树坑,手上起过血泡的,掉皮出血的,前三届的学生估计每一个都逃不掉,据说真有女生偷偷哭鼻子,但我没亲眼见过。很奇怪,那时很少有逃避劳动课的学生,包括那些“吃皇粮”的干部家庭子女,个个照样干。
算下来,学校先后挖成上万个树坑,种上了松树、桉树和橘树。种完,要提水浇,从校门口井里或山上水塔池提水,用洗澡的铁桶或塑料桶,力气大的提大半桶,力气小的提小半桶,一棵不漏要浇遍。松树成活率比橘树高,死树还得补苗。隔了一年,草长得比树苗还快,还高,又得除草。所以种好一棵树,真非一件易事。
山上的树种完,学校又想着种菜。辟出了三个菜园:一块在食堂前面,教学楼与学生宿舍之间夹的一块平地,足有七八亩;一块在教职工宿舍后面,是斜坡地,有三四亩;一块在食堂左侧种橘树的山头下方,右边紧邻公共旱厕,只有二三亩。三块地,食堂门口的经营得最好,教职工宿舍的次之,橘树山头下方的较差。
种菜是技术活,学生们不擅长,这个光荣任务交给了看宿舍的老向,也不知道有没有工钱。记得他分类分区种上成片的豆角、茄子、辣椒、黄瓜、苦瓜等,整整齐齐搭着架子,竖着爬蔓子的杆子,绿油油一片。开花时有花,有蝴蝶,有蜜蜂,挂果时硕果累累,长的,短的,青的,紫的,绿的,红的。那时候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景象,我们去饭堂,打菜地边走过,回宿舍,也得穿过菜地。真是好玩,居然弄成了一个菜园子学校。我们穿过菜畦行间,茂密的枝叶把身影遮得严严实实。
有一天中午下课时,我们见到老向躬着腰,正在转角的菜地教一位年轻姣好的姑娘移栽小白菜苗。姑娘动作有些稚拙,我们还以为是他女儿,在玩泥巴呢。后来老师告知我们一个爆炸性消息,这位姑娘竟然是学校董事长远在美国的小女儿,趁着放假回国省亲,特意来这里勤工俭学,体验生活。天啊,有这等事!这片不时飘着浓重粪水臭味的菜地,食堂腥臊污水渗流而过的菜地,黑泥巴黄泥巴糊糊无处站脚的菜地,校董千金却屈尊在那里,扎扎实实栽了一上午菜秧。
印象最深的是几次迎接学校董事长莅临,我们停课搞卫生,那狠劲是把里里外外洗得一干二净仍不算数,还要搓脱一层皮。记得每个学生提着洋皮铁桶,排一条长龙队伍,步行去镇上锯木厂装运锯末,回来洗地,跪在地上双手用锯末来回擦,水泥地板必须擦出一尘不染的水磨石般的反光。所有人脱掉鞋子,打赤脚或穿袜子才能进室内,走廊、宿舍、饭堂都是这个标准。我看见饭堂大师傅一律穿上白大褂,装模作样,特像医生,但又浑身不自在。
毕业后,我回过学校多次。当时的黄泥坡变成了亭台楼阁、花园水榭、绿树成荫,菜地当然一丁点也没有了,我们当时种在山头的树,蔚然成材,松涛阵阵。真是感慨,曾经以为虚度的时光,其实它像种下的树苗,当你走得很远了,蓦然回首,发现它已悄悄长成了一片森林。原来,时光里的一切都会自然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