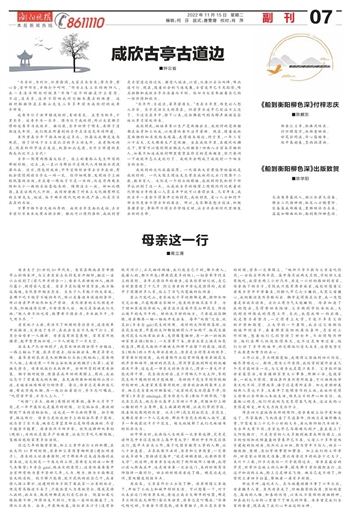■蒋立清
母亲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老家在衡南县茅市镇早山村西家冲,与父亲老家占禾村龙家冲相邻,翻过一座小山就到了(前几年并村合一)。母亲兄弟姊妹四人,她排行最小,颇得家人宠爱。老家多是红壤砂质页岩,地方偏远高峻,自然条件相当恶劣。生长于人多粮少的大家庭,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难以具备读书深造的条件,所以母亲早早地参加生产劳动。虽然母亲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但她通情达理,不甘屈居人后。她总是告诫我们兄妹:“做人要不怕吃苦,做事要不惜出力,井水挑不干,力气用不尽。”
老家地少土瘠,养活不了新增的青壮劳力,适逢改革开放搞活,父亲迫于生计,在我出生后不久南下打工,家里全由母亲一人操持。母亲没有丝毫畏难,家里家外地操劳,起早贪黑地忙碌,一个人顶起了一片天空。
后来生产队分田到户,我家水田抓阄分得十分偏远,一路上翻山下坡,农具背进去,稻谷挑出来,都是异常之难。最笨重的农具是木制脚踩打禾机(脱稻机),需要两个人抬,上面还有一个防止谷粒溅出的棚子(木罩)。我家缺乏劳力,母亲就把打禾机拆开,分部件背到田里再拼装。棚子相对较轻,便落在我年幼的肩膀上,因此,我永远忘不了背着庞大的木棚,在充满荆棘和树枝的山间小道,左磕右碰艰难前行的情景。每次,母亲总是要折返几趟,帮我背起木棚,再一起拉扯着前行,并不忘叮嘱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双抢”(杀禾、插秧)要跟时间赛跑,每年七月中下旬,是一年中最忙也是最热的时候。打完稻谷后,要挑回刚脱下来的湿稻谷粒,这也是一件头疼的事情,担子颇重,路远难行。母亲总是给我担子上的稻谷尽量少装些,说压重了长不高,她自己箩筐里却总是堆得满满的。尽管千般苦万般累,母亲依然不辞辛劳,毅然选择种双季稻(晚稻),为的就是能多产些粮食,让我们多吃几顿饱饭,售粮后能给家里多些活钱。
经过几年的勤劳苦做,加上父亲外出打工的积攒,在我大约10岁的时候,母亲和父亲商量砌新屋(建红砖房子)。原来的土坯房要推倒,对于那些年还未通马路的我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庞大的工程,需要巨大的决心和勇气来架势(乡音念gáxí,做决定的意思)。这意味着要集中全家所有的力量辛苦好几年,人力、财力、物力方面都是巨大的消耗。钱不够只能借,能不花钱的就自己干,或者请人换工帮忙。运建材的车子到了离我家一公里的地方,便没有马路进不来了,只能依靠人力肩挑背扛。煤炭是请人挑的,挑石灰、做泥砖都是我们自己担当。烧窑如果火候把握不好,师傅功夫不到位,可能一窑砖就报废了,又得从头再来。后来,开屋场地基,筛红岩石沙子(没有余钱买河沙),正式砌砖码墙,我们能自己干的,都不请人,能请人的,都不外包(那要花更多的钱),一切崇奉节约至上的原则。当年正值壮年的母亲,后来经常回忆说,自己当时整整瘦了十几斤。但父母亲的辛苦也是值得的,我家早于周围许多人家,住上了洋气而宽敞的红砖房。
靠山只能吃山,老家地处干旱的衡邵走廊,耕种水田交完公粮,只能勉强自家糊口,能卖的余粮实在不多。为了增加家庭经济收入,母亲没日没夜开荒山种花生。附近山坡平的或不平的,好的或不好的地方,只要能站住脚跟,母亲都要一锄一锄地开发出来。每年“双抢”之后,就是扯(乡音念qiǎ)花生的时候。彼时的太阳特别毒辣,站在花生地里,早晨的太阳都能晒得人汗如雨下。把花生藤连同花生从地里扯出来,先将藤蔓捆好,再一担一担地挑回家里去摘(脱粒)。一天劳累下来,母亲衣裳上满是白色的盐渍,那是无数的汗珠被太阳烤干后留下的痕迹。摘花生(脱粒)的工作大部分在晚上,母亲是全村有名的快手,常常要忙到深夜,我的暑假作业经常伴随着母亲摘花生的声音和动作。摘好的泥花生,得用箩筐挑到附近的池塘淘洗干净。这也是一项巨大的体力活儿,得出一身大汗才能洗得干净。花生淘洗好后,至少得晒几个大太阳,等到花生肉干脆的时候才能收储。存好的干花生等到价钱相对较好时,或者家里需要用钱时,母亲就会挑到集市上去卖。她总是自豪地对顾客说:“我家的花生洗得最干净,你郎家(乡音念nǐnāngā,意为你老人家)要给个好价钱。”每次卖完花生,她总会从集市上买回小干鱼,用猪油炒上精心腌制的干豆角鲊,装上满满的两罐,让我们带到学校,改善住校期间的伙食。从点(种)花生到扯花生、卖花生,大都是母亲一个人完成的。那些年卖花生的收入尚可,最多一年收获近千斤干花生,极大地缓解了我们兄妹读书的经济压力。
初中毕业时,我面临人生的第一次重要选择,究竟是读师范中专还是继续上高中考大学?那时中专师范还很流行,能早点出来工作,属于吃国家粮有工资的人群,让人十分羡慕。正在犹豫不决时,母亲和父亲商量,一定要让我多读书,坚持读完高中,“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考大学”。就这样,母亲亲自送我到了衡阳城郊三塘镇,我得以进入衡南五中。这是母亲第一次出远门,来的时候有老师陪伴一路同行,回去的时候母亲迷了路,硬是边走边问,靠双腿走到搭车点。
再后来,父亲在外打工立住了脚,母亲便随父亲南下,开始了工地上和城中村的生活。可以想象一下,对于从未出远门的母亲来说,要适应南方大都市的喧嚣,那是多么的慌乱无神啊!每次电话里,母亲总是叮嘱我:“你要吃饱吃好,不要舍不得花钱,读书费脑子,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营养一定要跟上。”她却只字不提与父亲省吃俭用,一分钱当作两半花。高中每月放两天月假,学校停火没有饭吃,我得坐两三小时汽车,再走一小时的路回到老家。母亲南下的日子,月假我只能寄居亲戚家,返校时想着父母离乡背井辛劳备至,同龄人早已打工赚钱,无需父母操心,我的眼泪竟然夺眶而出。脚步走得很是沉重,我一度想着是否放弃读书,去打工有力气又能赚钱。母亲知道了我的想法,急得要回来陪读。父亲跑到学校安抚我,又找到老师做我的思想工作。自此,我想我唯一的出路,就是努力再努力,一定得考上大学,才能不辜负父母的辛劳和期望。上大学的一个暑假,我去过父母租住的城中村房子,看着那里简陋的居住条件,恶劣的工作环境,想着他们已经坚持了好些年,不由得黯然神伤。他们在那儿纵使住得再久,也不过是匆匆过客,他们打拼了多年的城市,终究跟他们毫无关系,这愈发坚定了我要更加努力的决心。
工作以后,手头稍微宽裕,我便将父母接到四川同住,略尽孝顺之心。期间,因为工作原因,我经常到国外出差几个月才能回来一次,与父母亲也是聚少离多。父亲依旧接些家装零活,母亲操持家里大小事务,照顾小孩,包揽家务,一刻也不得闲。居住条件虽然有所改善,可川湘两地毕竟文化不同、习惯迥异,语言还是有所差异。加之亲朋好友相熟人员也不多,又离开了能够劳作的土地,我始终觉得父母难以全部融入本地生活,难见往日的开心和自信。我最揪心的是,他们对我的态度变得客气起来,这让我的心里很是难受,却又无力改变些什么。
待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绵阳,母亲离故土似乎更加遥远了。尽管高铁、飞机改善了交通条件,但她总是嫌价格太贵,宁愿乘坐二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再从衡阳转汽车回乡。与当年大有不同,老家也早已马路硬化到户,甚至装上了太阳能路灯,只是老家的人大多搬到城里或附近镇上,往日的喧闹和炊烟袅袅的景象早已不再。父母三十多年前双手建起的红砖房,依然屹立如初,因为常年不住人,回去一趟收拾、整理、清扫等琐事愈加繁杂。加上我们的工作牵绊,回老家必须做足准备,因此母亲还乡的机会少之又少,来川十三载,归乡次数仅一只手数得过来。母亲在最后的岁月,时常怀念故土的人和事,提及那片曾经摸爬滚打、流过汗和泪的土地,脸上总是神采飞扬。她自己走不动了,却督促父亲回乡扫墓,帮她看一看家乡新貌。
命运多舛,造化弄人。在与病魔顽强斗争了六年之后,母亲撒手人寰。虽然母亲走了,但她勤劳的品质、坚韧的意志、高尚的人格、和善的性情,以及从不畏难的湖湘精神,却在我们儿女的心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母亲曾是我们全家的脊梁,现在成了我们心中永远的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