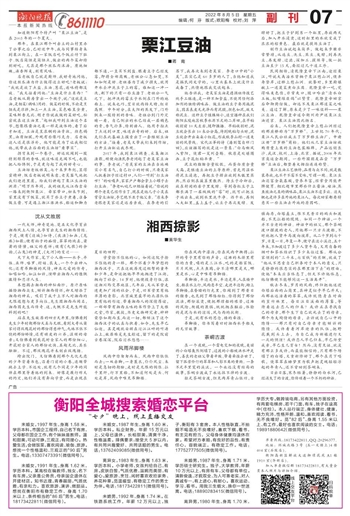■黄华生
沈从文故居
一代大师,神奇楚地。楚巫文化孕育出湘西风土人情,也孕育出先生的湘西情结。于是,便有《边城》如诗,《夜渔》如画,《龙珠》如歌;便有柏子的痴情,翠翠的纯真,萧萧的懵懂,祖父的慈祥;便有《九歌》的余韵,《山鬼》的神灵,《大河》的变迁……
天下大作家,笔下小人物——水手、卒伍、巫师、喽罗、村姑、农夫,一个个出神入化;还有吊脚楼的风情,神巫之爱的传奇,如唱如吟,如泣如诉,演绎出湘西人的慷慨激情和悲凉人生。
本想揭去湘西的神秘面纱,原汁原味描绘湘西众生,倾诉湘西情怀,却又增添了湘西的神采,吸引了成千上万人对湘西的无限遐想与更多向往,先生因湘西而闻名,湘西因先生而传奇。这,大概不是先生所能料到的吧?
站在先生故居的四方天井里,仿佛看到先生少年时期那份天真与无瑕,看到大哥从萧家讨得玫瑰花时的那份得意神气,九妹不依不饶的那份矫情,还有顽皮的六弟,温顺的母亲;又仿佛看到栽花时全家人的那份细心,开花时全家人的那份欢快,其趣无比,其乐融融。不过,那玫瑰花并未制出玫瑰糖。
跨出院门,又仿佛看到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背着书包,沿着门前的小巷,连蹦带跳去上学。不远处,就有几个同是少年的同伴在那里等着他的到来。好像是履行昨天的约定,他们并没有奔向学堂,而是出现在夏日的田野。
学堂拴不住他的心,如同这院子拴不住他的身一样,那个怀着少年梦想的湘西汉子,只在这故居度过短暂的童年和少年,是命运把他早早地抛进了江湖,抛向了社会。14岁时,他便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交界地区,几年后,又从军营走进更加广阔的社会。于是,旧军营里有他单薄的身影,北京城里最早的北漂队伍里有他的形迹。带着湘西人的深情厚谊,一部部带有湘西土味的书作登上了大雅之堂,作家,教授,历史文物研究者,种种荣誉如期而至,而这一切,都倾注了这个湘西汉子的认真与执着。如今,先生早已仙逝,其灵魂就安顿在沱江江畔的听涛山上,故居难觅先生踪迹,留下的是院前古巷深深,院后沱水悠悠……
风雨吊脚楼
风雨中你匆匆而来,风雨中你依依而去;一双赤脚,一身蓑衣,仆仆风尘。来时是急切的期盼,走时是无限的惆怅。拉千里纤,行万里船,不知道何处是头、何处是岸,风雨中唯见吊脚楼。
你在风雨中漂泊,你在风雨中撕搏;拉纤的号子里有你的声音,过滩的木排里有你的力量,喝的是三江水,吃的是船家饭。片片风帆,点点鱼鸥,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水,心灵中唯有吊脚楼。
吊脚楼,半边是水,半边是岸,人在楼中坐,船在水上行,风雨悬半空。走进半边街,踏上吊脚楼,在昏暗的灯光里,你闻到了那昔日的脂香,也见到了那缕粉红。你得到了那份混浊,那份滚烫,便把那撑船的艰苦,过滩的风险,爬桅的畏惧,统统抛在脑后,体验的是泥与水的渲泻,风与雨的抗衡。
于是,就有水的思念,楼的牵挂。
吊脚楼,你书写着旧时湘西水手船夫的无穷故事。
茶峒古渡
在一个夜晚,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美丽的小白塔轰然倒塌了,过渡的小船被洪水冲走了,善良的老祖父带着辛酸、带着牵挂去世了,留下孤苦伶仃的翠翠和人影不离的黄狗。一条不足半里宽的溪流,一个永远没有结局的故事,茶峒古渡成了永远抹不掉的古渡。
驻足茶峒古渡,但见两岸青山依旧,古镇尚存,白塔矗立,惟不见昔日的码头和渡船,不见拉船的缆绳。如同一个神话,一个并不古老的神话。神话中的祖父,那个茶峒渡口摆渡的老人,用他那一只方头渡船,不时地把人货牛马渡向彼岸,从二十岁到七十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便守在这小溪边,五十年来,不知渡过了多少人货牛马,又用自备的烟叶和茶水结识了多少来往过客。那从公家领到的“三斗米,七百钱”的月酬,就成了“他从不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的理由,使他“本来应当休息了,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生活离开”。
秋去冬来,岁月的风雨,终归把他送进白塔后面的山岗里,其神灵似乎早已升天;而那永远活着的翠翠,或许就隐身在对面的篁竹林里,每日注目溪面的薄雾,等待着远去恋人的归来?或许正在寻找自己的母亲,那个生下自己就死去了的母亲,那个为夫殉情的母亲,去诉说自己心中的隐情——那只有对自己母亲才能倾诉的隐情。或许看着河岸迎亲的队伍,把野花戴到头上去,为自己成为新娘进行又一次的预演?或许恋人早已归来,早已拜堂成亲,早已生儿育女!然而,没有见证,就没有那么多或许,而最能相信的,只有那个坍塌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日出日落,寒冬酷暑,静静的白水河,已经消失了的古渡,你传颂着一个不朽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