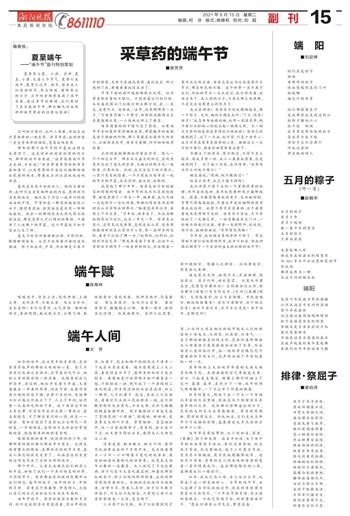■文 芳
如今的端午,关注更多的是亲情,是母亲亲手张罗的那份沉甸甸的心意。前几日母亲打电话过来询问,过节喜欢吃什么,她和父亲好提前做一些准备。我随意说出几样简单、清淡的,她似乎觉着不丰盛,又连着报出一串鱼虾肉蛋,问我可好。我装作很感兴趣地回答不错,分量少弄些吧。电话那头忙兴高采烈地应下了。人上了年纪,似乎整一大桌好吃的给下辈,成了母亲过节的头等大事。尽管近年我对大餐一事渐淡、甚至渐倦怠,可了解长辈们的心情,终是一一迎合。有时还想老了是否也应当研究一手好菜,一手妈妈菜,这样孩子也许会时常想起回家,想起母亲和她的美食呢。
朦朦胧胧的童年、恍恍惚惚的少年,仿佛所有的精彩都与那些节日有关。也许是物质匮乏的缘故,在那些欢快的节日里,最让人难忘的就是美食了,而品尝这些美食的过程自然成了当时全部的快乐。
那个年代,父母无法满足我们物质上的丰富,却给了我们一个异彩纷呈的世界。不同的节日,母亲都会在别致的氛围中让我们难忘:春节的饺子、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饼。母亲是个很睿智、贤惠的人,总能以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生活是幸福的。
端午节前夕,母亲会提前准备许多食材。粽叶先放到清水里浸泡着,用往年的红枣、红薯干、花生和晒干的桂花洗干净煮一下也在水里浸泡着。糯米需要泡上三天三夜,看发得差不多了,最神圣的时刻才真正到来。看着她灵巧地将两片粽叶错叠在一起,只轻轻地一扭,便形成了一个碧绿的三角形的盅,用手将浸好的米放在盅里,加上一颗枣、几片红薯干、花生,再放上几粒桂花,看着它们五颜六色地挤在一起,我们的眼里顿时发出亮光,口舌生津。当热气腾腾的锅盖被揭开时,刚才嫩绿的小荷包变成了墨绿色的“小胖猪”,糯糯的、甜甜的,裹在翠生生的叶子里,紧紧糍糍。急急地扯开,咬一口塞满腮帮子,烫烫的,吞又吞不下去,吐又舍不得吐出来,看得大人又好笑又心痛。
还有咸蛋,瞅来瞅去,瞅大个的、看得见红油黄溢出的下手剥开来,先是皱着眉头一小口一小口咽着不爱吃的咸蛋白,最后细细品味着好吃的油蛋黄;红苋菜是端午必备的一道蔬菜,大人说吃了不生红眼病。孩子们是不大爱吃蔬菜的,却喜欢那紫红的菜汁,拌上米饭别样得好看,也就别样得有趣觉着好吃;压轴的是红烧肉与烧鲢鱼,分量不多,有客人在时,孩子们不敢多伸筷子,可又经不起诱惑,只有趁父母不注意时偷偷夹一大筷,急急咽下。
三口两下扒完饭,孩子们就聚到院子里,小伙伴之间互相比拼起早起大人们给佩挂的小香包来,比颜色、比造型、比香气……至于那些甜腻歪的绿豆糕、芝麻糕最终都被大人领着孩子恭恭敬敬地送给了长辈,然后由老人慈祥地打开,拈一块给身边眼巴巴守望着的孙子孙女们,笑声便溢满了平房院落的一砖一瓦。
屋角矮柜上大海碗中养着的大朵大朵莹白栀子花,在湿漉漉的空气里氤氲生香。窗口、门板甚至鸡笼、猪圈上都斜斜插上了艾叶、菖蒲、蒿草,在烈日下一晒,端午的阳气嗖嗖腾升,一下子拉开了仲夏的帷幕。
许多的夏天,构筑了我一个又一个幸福而丰富的生活梦境,使我至今只保留快乐在童年的记忆里。我依稀记得那遥远的日子,炙热的太阳光与我耳鬓厮磨,有清新有期盼,有深刻有浅淡。但我知道,它们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影像,盛装着我太多无法抹去的年少心情。
端午节是有故事的,从小就知道:屈原、《离骚》、粽子和龙舟。后来才知道,关于端午节的由来有很多说法,有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胥说、纪念曹娥说、起于三代夏至节说、恶月恶日驱避说、吴月民族图腾祭说等。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间美味和母亲的慈爱一直伴随着我们,走出那段黯然的心境,簇拥着我们一路前行。
如今,我也已为人母,女儿远方求学,也带走了我一样爱她的心。今年的端午节,女儿选择了在学校就地过节,浓浓的亲情因为有爱而天涯咫尺。“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生。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愿我们国家山河无恙,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