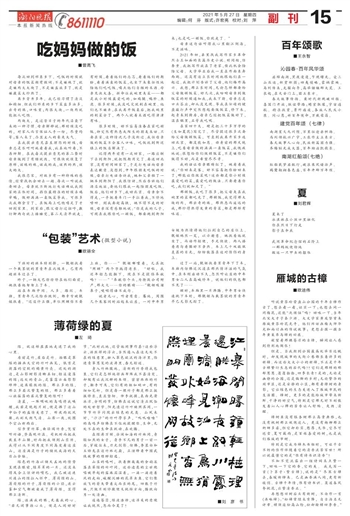■曾高飞
每次回到祁东乡下,吃饭的时候就对母亲的饭菜颇有微词:不是嫌辣了,就是嫌肉太大块了,不是嫌盐放多了,就是嫌蔬菜太炒熟了。
离乡背井多年,我已经习惯了清淡和精细。但我们祁东的乡下菜盐多油多,出奇的辣,口味重;肉很大块,一块肉就能把人吃饱。
肉块大,是过苦日子的年代沿袭下来的一种习惯。母亲解释说:那时候没吃的,对家人而言保证人手一份,尽量均等;客人来了,凸显主人的豪爽大气。
在我提出意见甚至埋怨的时候,母亲总是乐呵呵地看着我,认真地听着,不再辩解。在我每次提出意见的第二餐时母亲做到了有错就改,可很快就恢复了原样,该辣的辣,该咸的咸,该熟的熟,该大的大。
我很恋家,对故乡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经常找机会回去一趟。每次一听说我要回去,母亲就不断地打电话确认我到家的具体时间,掐住最精准的时候杀鸡宰鸭,做好满满一桌饭菜等我。可很多次我都食言了,在饭局上吃饱喝足了才回到家里。到家后,跟父母打过招呼,敷衍聊两句就上楼睡觉,第二天清早就走。有时候,看着他们的忐忑,看着他们的期盼,看着满桌的饭菜,也坐下来象征性地陪他们吃吃饭,喝点他们自酿的米酒。母亲见状大喜,拼命往我碗里夹菜——都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如鸡腿、鸭胗、鱼泡。很多时候,我没吃完就剩在碗里。他们也不嫌弃,在我离开饭桌后,把我碗里的剩菜分了,两个人就着米酒吃得津津有味。
很多时候,好不容易准备在家吃顿饭,却突然有熟悉或陌生的朋友来访。只要在家,这种情况几乎没断过。我怕母亲做的饭菜不合客人口味,吃饭就到附近镇上的饭店解决了。
记得两年前有一次回家,一路应酬下去到衡阳,就把假期用完了。要返回北京,没有时间回家了,于是打电话向母亲表达歉意。没想到,中午跟朋友吃饭的时候,母亲打电话告诉我,她和父亲租了一辆车到衡阳了。我很惊讶,然后告诉他们酒店地址,要他们跟我一起陪朋友吃饭。饭后,他们回乡下,我回北京。母亲舍不得走,一手把着车门一手拉着我,不停地唠叨。到我要赶高铁,她不得不走的时候,母亲深有感触地说:“你是我的儿子,可现在我跟你吃一顿饭,都要跑到衡阳来;也是吃一顿饭,你就走了。”
母亲这句话听得我心里翻江倒海,不是滋味。
2021年初,县里找我写作家乡革命烈士王如痴的长篇历史小说。时间短,任务重。我把写作放在了老家,借此机会陪陪父母。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外面东奔西跑,还没有这么长时间地跟他们在一起过。我把计划告诉了父母,他们格外高兴。我想,那么长时间,无论怎样都要给父母做顿饭菜。好几次,我吩咐母亲到做饭菜的时候通知我,我来下厨。母亲总是口头答应,却从没兑现。等我在忙碌的键盘敲打声中突然想起要做饭菜,停下来,起身来到厨房,母亲已经把饭菜做好了,温在锅里,正等我吃呢。
在家四十天,硬是把三十多万字的《生如夏花》写完了。尽管提过很多次要给父母做顿饭菜,可直到我离开家乡返回北京,都没能如愿。动身前的那天晚上,吃着母亲做的满满一桌饭菜,我愧疚地说:很想给你们做顿饭菜,不是嫌你们做得不好,而是希望尽尽孝。
我的话让母亲眼睛红了,她看着我说:“你回来是客,好不容易把你盼回来了,哪能让你做菜呢?这些都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菜,最爱吃的做法。只要看着你吃,我们就知足了。”
那顿饭,我吃了很多,把父母夹在我碗里的菜都吃光了。那顿饭,我觉得那大块的肉,那出奇的辣,那熟悉而遥远的咸,那炒得熟得发黄的青菜,都是那样有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