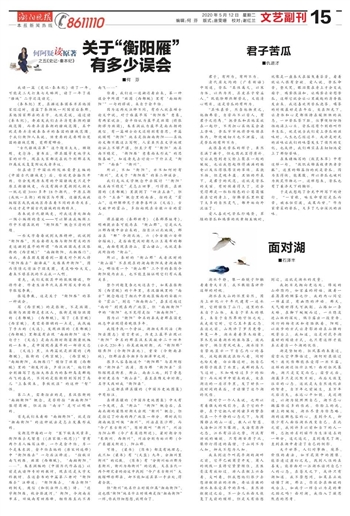我读一篇《史记·秦本纪》读了一年,可能是三天打鱼七天晒网,读了一年了连“疆域”二字还没读完。
《秦本纪》里,在描述秦国吞并其他国家经过时,透露了秦朝统一列国前后秦郡、其他国家郡县的名字。也就是说,通过读《秦本纪》,要启发我们去弄清楚秦朝的疆域范围。而要弄清秦朝的疆域范围,其中就是要弄清被秦吞并的各国的疆域范围。于我们衡阳人来说,顶重要的是要明白楚国的疆域范围、楚郡有哪些。
“古代疆域沿革”这个题目太大,顾颉刚、史念海、童书业、谭其骧等史地学大家的旧作,现在大家都还在就个别郡名及归属反反复复附议或者异议。
但在读了中国社科院林荣贵主编的《中国古代疆域史》后,你就更会豁然开朗。你会发现原来有的中国疆域史只是中原王朝疆域史,而没有揭示夏朝到元朝大一统之前3000多年18个朝代。中原王朝(或统一王朝)的辖区与外围、边疆民族政权辖区或民族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共存关系,而这才是中国古代疆域的结构特点。
再来说古代疆域史,对我这身处湘南一隅小编辑的意义——可以解决我编辑工作中不堪其扰的 “衡阳雁”概念不清的问题。
一些文字每每说到大雁精神,就说到“衡阳雁”,然后要将大雁与衡阳有关的历史追溯到最早的所谓“西汉班固或东汉张衡的《西京赋》”“南翔衡阳,北栖雁门”。由此,再在朋友圈看到一圈友对个别人将“衡阳雁去”翻译成”大雁离开衡阳”,因而愤愤之情溢于朋友圈,更是哈哈大笑,看来不堪其扰的不止我一人啊。
首先,我们反驳其中的低级错误,即将作者、作者生活年代或其所写文章的名字张冠李戴。
张冠李戴,这是关于 “衡阳雁”的第一种误会。
写《西京赋》的是张衡,不是班固。张衡与班固都是东汉人,张衡是模仿班固的《东都赋》《西都赋》,写了《东京赋》《西京赋》。更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找遍了手头的《文选》,发现班固的《东都赋》《西都赋》里都没有出现“南翔衡阳”这个句子!《文选》是南北朝时期梁朝萧统编的一本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文选》里,头两篇就是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西京赋》 “南翔衡阳,北栖雁门”模仿了班固《西都赋》里的“朝发河海,夕宿江汉”。他们都分别描写了包括大雁在内的各种鸟类群起而飞的盛况,不同的是张衡特别写到了鸟儿“上春侯来,季秋就温”的这种“智”性。
第二点,需要指出的是,东汉张衡的“南翔衡阳”概念,是否特指“湘南衡阳”值得商榷,但泛指“南方”是可以明确的。
首先我们来看称“南翔衡阳”,就是指“湘南衡阳”的这种说法是怎么发展形成的。
宋朝范仲淹的一句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渔家傲·秋思》)”曾有两个名人编写注释,一个是俞平伯,另一个是朱东润。俞平伯在他的《唐宋词选释》中“衡阳雁去”一句后注释道:“指秋日南飞的雁。班固《西都赋》,‘南翔衡阳。’……”。朱东润编的《中国历代作品选》以前是我读师专时的教材,现在还是大学文科教材。在这套书的中篇第二册对“衡阳雁去”注释道:“衡阳雁去,‘雁去衡阳’的倒文。庾信《和侃法师三绝》诗:‘近学衡阳雁,秋分俱渡河。’衡阳,今湖南省市名,旧城南有回雁峰,相传雁至此不再南飞……”
你看,我们这一追溯还看出来,第一种误会中所谓“班固《西都赋》里有‘南翔衡阳’”一句的谬误,来自于俞平伯。
因为这两处注释不同,有些人就在硕士论文中说,对于谁最早写“衡阳雁”意象,有两家说法。俞平伯认为最早是班固(将张衡谬为班固),朱东润认为最早是南北朝的庾信。有一篇硕士论文还特别有意思,开篇就阐明“衡阳”地名是指湘南衡阳——其他论文都不敢这么写啊,人家虽然在文学地理论证上不够严谨,但至少有“‘衡阳’地名尚不稳定,‘衡阳雁’意象尚未形成”的思维基础”,知道要先去讨论一下什么是“衡阳”“南岳”“衡州”。
所以,不知“衡阳”,亦不知何时有“衡州”,是关于“衡阳雁”的第二种误会。
我们先从文学概念中去探讨“‘衡阳’地名尚不稳定”是怎么回事。巧得很,在班固的《东都赋》里提到了“四渎五岳”。但这个“五岳”概念里的南岳,指的是“霍山”,这种解释见于唐李善所注《文选》。古文献中的霍山,多指向现在安徽六安的霍山。
谭其骧的《秦郡新考》《秦郡界址考》,明确提出秦可能存在 “衡山郡”,它是从九江郡西境中分出来的,指长江以北地域,郡治在 “邾”今湖北地。六(今安徽六安部分辖地),是后面楚汉时期九江王英布的都城,南面有现在潜山、霍山诸山,也就是秦汉所指的“衡山”。
所以,秦时的“衡山郡”或者汉时的“衡山国”不在现在的湖南衡阳或者湖南衡山,哪怕有一个“衡山郡”三个字的秦简今衡阳境内出土,也不能直接证明它们有从属关系。
整个问题复杂之处还在于,如果在张衡写《西京赋》的十年里,东汉疆域里的“南方”概念越过了相比中原地区偏南的安徽六安“霍山”,到达“湘南衡山”,甚至还越过“南岭”到现在两广地区,但“南翔衡阳”中的“衡阳”也不见得是指 “湘南衡阳”。
因为以“衡阳”命名的县或者郡在国史地志中出现得要晚很多年。
我随手找一个旁证,湖湘文库同治《衡阳县图志》前言考证,历史上最早出现以“衡阳”命名的郡在汉末汉献帝二十四年(公元220年)孙吴政权时期。此“衡阳郡”辖烝阳(今衡阳县地)、重安(今衡南县地),但郡治在今湘乡与湘潭市之间。
很多人容易把这个“衡阳郡”与其所辖的“衡阳县”混淆。因为那 “衡阳县”实际辖现在衡东、衡山、南岳三地,到了晋惠帝时更名为“衡山县”。甚至在隋文帝时期,名字又改回成“衡阳县”。
上述都在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有标注。
在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又有一个发现,在“衡山”“衡阳”概念后,在南北朝的梁陈时期又出现“衡州”概念,但是指过了岭南的两广地区一部分。那时我们湖南地区叫做“湘州”,州治在长沙郡。而“今广东古衡州”,陈时期叫“衡州”,州治为阳山郡(今广东英德附近),梁时期分为“东衡州、西衡州”,州治分别为始兴郡(今广东韶关附近)、阳山郡。
可惜,《梁书》《陈书》都没有地理志,我只知《梁书》有“(天监)九年,分湘州置衡州”的记载、《陈书》有“分衡州始兴郡为东衡州,衡州为西衡州”的记载。又在当代一两个研究者的论述中找到“今广东古衡州”大致辖哪些郡县,却不能知道其第一手出处,得看全貌。
但“衡州”地名什么时候归属“湘南衡阳”, 这也跟“衡阳”地名什么时候确是指“湘南衡阳”一样,你我仔细想想,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