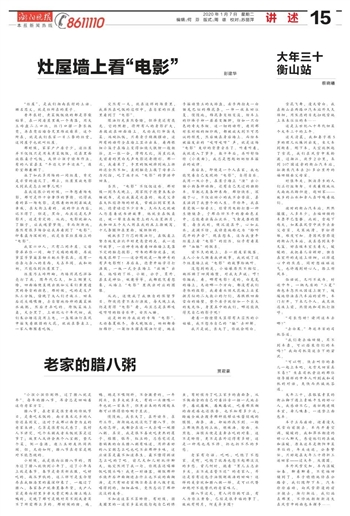“灶屋”,是我们湘南农村的土话。顾名思义,就是灶所在的屋子。
昔年农村,煮菜做饭烧的都是茅柴稻草。在一间房屋里截一个角落,用大土砖盘二三口灶,灶门口摆一条长板凳,再在凳后墙旮旯里堆放柴草。这个所在,就是我们农家一日三餐的灶堂,这间屋子也就叫灶屋。
那时候,家家户户房子少,这灶屋并不仅仅只是用来煮菜做饭,还在里面放张桌子吃饭,或供小孩子读书作业。有的人家甚至“半边火炉半边床”,连卧室都兼顾了。
派了如此多用场的一间灶屋,肯定是非常的逼仄了。那么,灶屋里放电影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一年想看场电影,那可是件十分奢侈的事情。记得我看的第一场电影,是跟着奶奶到县城走亲戚,在大街上看的。放的什么内容,记不得了。但是,黑白,而且还是无声影片,这是肯定的。从此,电影就融入了脑子,让我魂萦梦绕。幸而渐渐地,居然有很多场合让我再看到了“电影”。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自家灶屋墙上的“电影”。
我家六口人,只有二间半屋。父母带弟弟住一间。砌了关鸡的鸡莳,再放箩筐芋箩簸箕锄头耙头等农具,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又占半间。我和奶奶,只能住到灶屋里了。
灶屋乃土砖所砌,内墙用泥巴拌谷壳打了底,因年代已久,加上烟薰火燎,四面墙便呈现出犹如父辈们黄里透黑的脊背的颜色。那时候,吃的是生产队工分饭,傍晚了大人们才收工。回来后还关鸡喂猪,去自留地给种的蔬菜淋水施肥,然后才弄吃的。待饭菜端上桌,天全黑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朱公塘还没用上电,一盏煤油灯在风中摇曳着微弱的火花,就放在餐桌上,一家人都围着吃饭。
突然有一天,就在这样的场景里,我居然在吃饭的过程中,在自家的灶屋里看到了“电影”。
煤油灯光虽然昏暗,但毕竟还有亮光。它的照射,将所有人的身影扩大,再投放在四面墙上。无论我们伸筷夹菜、端碗扒饭,只要身子稍微摆动,这所有的动作全在墙上显示出来。看两根细小筷子在墙上变得如烧火铁钳一般粗壮,且一张一合,滑稽无比,简直比我先前看的黑白无声电影还要精彩。那一次,我看呆了,手里的饭碗掉到地上摔碎还全然不知,直到脑壳上挨了母亲二力坨指,吃了痛才从“电影”的梦游中回来。
当然,“电影”不仅仅这些。那时候一到冬天晚上,周家院子德贵来朱公塘说书,是让我最是欢喜的。他是父亲在大队经济场的好友,常被拉到家里来玩。德贵读过不少古书,久而久之就被人怂恿着说书讲故事。他就坐在饭桌边,被一帮坐在板凳上的人众星拱月,我和四五个大人则在我的床上捂被窝,十几条腿伸在里面,暖烘烘的。
被挑长了灯芯的煤油灯,在饭桌上努力地发出比平时更亮堂的光。我一边听故事,一边神奇地看着四面墙上晃荡不定的脑壳投影,听书的那份欢喜,就越发浓郁了——这分明就是一场神奇的有声电影啊!再后来,德贵开始学习打渔鼓,一板一式全在墙上“放映”出来。他唱的丫环、小姐、公子、员外,甚至是神仙、妖魔等等,我都能凭着想象,从墙上“电影”里找出对应的图像。
从此,这便成了我独自的保留节目。即使德贵不来打渔鼓,每天晚上我仍是有得“电影”看,而且总是在那吱吱呀呀的轻音乐中,安然入睡。
这是奶奶为我放的专场“电影”。无论春夏秋冬,每天晚饭后,奶奶都要纺棉纱。一架纺车摆在煤油灯前,她左手摇动竖立的大转盘,右手两指夹一白猫尾巴似的棉花条,一伸一收来回往复。慢慢地,棉花条变短变没,纺车上的纱棒子却一层层变臃肿,仿如一只白色的奇大枣核。这一切的动作,连同那时长时短的细纱线,都被放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然后映在身后墙上。而纺车被摇发出的“吱呀吱呀”声,就是这场“电影”美妙的背景音乐了。听着听着,我就进入了梦乡。数十年后,再听舒伯特《小夜曲》,我总是想起奶奶纺车摇出的旋律。
再后来,即便是一个人在家,我也能凭着自己发现的“电影”,自得自乐。我用一双小手,在屋子墙上“演”出小猫小狗各种动物,还有自己见过的独轮车、犁耙之类各种东西。那份快乐,深植于心,不仅让幼小的我不会苦寂,甚至滋润了我整个的人生。早些年,我在东莞做一份普工,经常用电轮打磨一种生锈链条,于那凸凹不平的磨面色差中,总能看出高山流水、飞禽走兽的图案。每当此刻,便沉浸其中,心如止水,波澜不惊,我诗意地称之为“聆听花开的声音”。现在想来,这与我童年灶屋上看“电影”的经历,似乎有着某种“血脉”的联系。
前不久的晚上,去一朋友家做客。主人小女儿缠着我讲故事,我就说了这个灶屋墙上放“电影”的故事给她听。
没想到的是,小姑娘居然不相信。她环顾了四周墙壁,对我大声说:哼!你骗我。看,哪有电影?是的,白晃晃的墙上,无论哪一个方向,都没有我们身体的投影。我看看头顶天花板上众星拱月似的二大数小的灯们,再瞧瞧四面雪白的墙壁,整个房子就仿如一个巨大的发光体,身置其中的我们,哪还能找得见自己的影子呢?
看着一脸憧憬又显得有点茫然的小姑娘,我不想为自己的“骗”去辩解。
我只是说,长大了,你就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