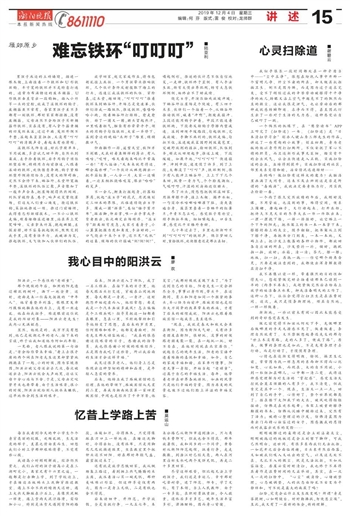男孩子床边的土砖墙缝,插进一根木楔,上面挂着一个铁环和U形铁丝钩。半寸宽的铁环并不是特意打造的,通常为布满锈迹的废弃桶箍。U形铁丝垂直弯出一段钩柄,插入小竹竿一头的空腔,就成了滚铁环的钩子。废桶箍虽不常有,每家男孩子差不多都有一副铁环。那时家家都拮据,没有废桶箍,父母决然不会给孩子买新桶箍作铁环。实在没有,有人拿个箍黄桶的旧篾环来滚,过过干瘾。篾环外侧不平整,滚起来歪歪扭扭,又没有“叮叮叮叮”的清脆声音,看起来有些滑稽。
滚铁环无师自通,好比学骑单车,不用说教,多尝试几回平衡,自然水到渠成。左手拎着铁环,右手用钩子顶住环壁后部,稍稍用力向前推送,人跟着滚动的铁环,欢快惬意奔跑。钩子紧贴环壁外侧持续给力,没有大的障碍物,定然不会停下来。晒谷坪、禾堂坪宽敞平整,滚铁环的队伍汇聚,声音像知了一般齐声合奏,把屋场搅得热热闹闹。列队穿梭阶基、巷子,响声欢笑萦绕屋场,引逗大人们童心焕发,抢过铁丝钩,笨拙地推送一程。推过门前塘坝,我得意忘形炫耀技术,一不小心铁环走偏,顺着塘墈滚进塘里,站在岸上哭哭啼啼。父亲拿来竹篙,挽起裤腿,左探右捞,好不容易挑起铁环,默默交到我手里,没有责怪半句。我破涕为笑,推起铁环,又飞快加入伙伴们的队伍。
放学回家,赶完家庭作业,将书包胡乱挂上床柱。一个男孩带头推响铁环,几个伙计条件反射般取下墙上的行头,迅速汇成滚铁环的队伍。穿阶基,过禾堂,趟田埂,“叮叮叮叮”推着铁环来到晒谷坪。开场总是竞速赛,伙伴们排成一路纵队,推送铁环,嘻嘻哈哈小跑,绕着晒谷坪打转转,愈走愈快。转了一圈又一圈,额头冒起热汗,口里喘着粗气,脑袋有些晕晕乎乎。领头的用钩子勾住铁环,大家一齐停下,滚到旁边的晚稻“禾虾子”堆里,稍稍歇口气。
仰面躺作一排,遥望天空,秋阳并不刺眼,天底衬着鱼鳞样的薄云。有人嘀咕:“哎呀,咯天看起来吗比平常高一些!”有人接话:“天本来就冇得边,哪会高些啰。”一个伙计从裤兜掏出一把牛筋红薯,一人分一片。大家一边嚼着,一边互相抓挠咯吱窝,爆出“哈哈”的笑声。
不一会儿,鲤鱼打挺起身,抖落稻草屑,玩起“滚8字”的花式。用泥块划定三四米的界限,比谁连续绕出8字多。围成一圈“拼蛋”,类似“锤子剪刀布”,跺右脚,伸右掌,唯一出手掌或手背者胜出,依次确定出场顺序。“滚8字”距离短弯度急,大家弓着身子,小心翼翼把握力度和角度。手法好的,一口气绕出十来个8字,还不见“死机”的迹象。候场的伙计猛喊“倒!倒!倒!”,喝起倒彩,推送的伙计忍不住自信地笑,一走神,铁环终于歪倒。有人手法生疏,转弯太慢出界犯规,转弯太急铁环侧倒,始终出不了好成绩。
绕完8字,开演压轴戏放坡冲坡。下晒谷坪往屋场是个陡坡,有三四十米长。伙伴们一个接着一个,从晒谷坪推动铁环,喊着“冲啊”,朝坡底猛冲。上段还能用钩子护着,中段只能追着铁环跑,下段要反转钩子摩擦内壁减速。滚到田埂平缓路段,勾起铁环,完成放坡。手脚不麻利的,铁环走偏,勾扯不住,滚进坡底菜园野刺玫篱笆里。突破野玫刺的挂扯,捡回铁环,队伍到齐,顺次从田埂起步,推送上坡。下段缓坡,如履平地,“叮叮叮叮”快速猛冲。冲到中段,速度慢了许多。到了上段,大都没了“叮叮”声,铁环侧倒,很少有人能冲上晒谷坪。上上下下几个来回,耗费一身力气,个个脸庞潮红,气喘吁吁,汗湿的刘海粘遮住额头。
尽了兴头,慢悠悠把铁环滚回家,用抹布擦干净,挂上木楔。揭开水缸,一勺筒冷水咕嘟咕嘟灌下肚,清爽袭遍全身。簸箕里叠着一沓晒干的红薯片,平素不怎么吃。感觉肚子有些空,顺手撕扯半块,细细嚼起来,口舌生津,感觉比平日格外香甜。
几十年过去了,乡里也渐渐听不到“叮叮叮叮”的铁环声。偶尔梦回儿时,重拾铁环,欢快惬意还是那么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