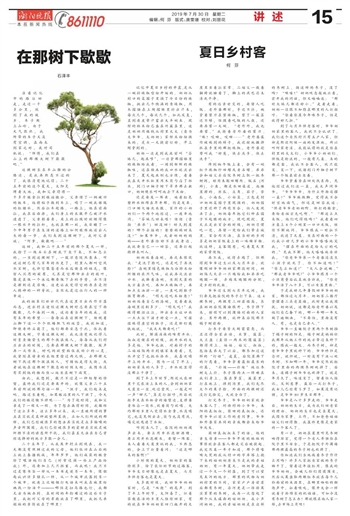记忆中夏日乡村的早晨,是从一碗抖辣椒噎粉开始的。奶奶从村口的菜园子里摘了今日份的辣椒,挑出几个饱满的青辣椒,用木擂锤在土陶擂钵里抖出汁来,每次几个,每次几个,如此反复,直到连皮带汁蓄出大半碗来。现榨的粗米粉已盛在竹簸箕里,这是奶奶用粮钱从村里太太(意为太爷爷、太奶奶)家榨米粉坊换来的,是头一天提前订好、早上刚拿到的。
奶奶一边走到我床前叫“芬妹几,起床哆”,一边拿那擂钵里的辣椒给我看。一闻到新鲜的辣椒味,还在赖床的我口水就流出来了。夏天起床倒也方便,看着我在天井水缸里用木筒勺舀了杯水,到门口柚子树下旱井那去漱口,奶奶便乐呵呵地去下米粉。
还是要发一阵呆。端着红色塑料水杯蹲在旱井那,仍是发呆。门口烟火塘洗衣服、家什的小奶奶们一个两个地经过,一连串地问:“芬妹几回来嗒?佬佬(意指‘弟弟’)回没回?好久到屋的?哪个去接的?爸爸妈妈回来没?”如果爷爷,或者奶奶的妈妈——老外婆恰好不在我身边,我就要自己一一回答,还要打起精神来叫人。
奶奶端着海碗,再次来催促我:“是洗了脸吃,还是吃了再洗脸?”海碗里绿色辣椒与白胖米粉纠缠的浓烈气味,让我再次流出口水。我捧着海碗,坐到天屋的大方桌去吃。再加点辣椒汁,再加点豆油拌一拌,一直吃到肚子肠胃都疼。“明天还吃米粉奥?”奶奶端着自己的海碗,笑着看我海碗里还剩多少。“明天吃!”我辣得眼泪汪汪,伸出舌头让口水一点点往下滴才好受一点,可揉揉辣得虚空的肚子,还是斩钉截铁地说,“我天天都要吃!”
此时,解渴消辣的唯有井水。叔叔还健在的时候,挑井水的大多是他。爷爷也挑。对面村子的二姑姑隔两日到娘家来看看,见水井空了也挑水添水。我喜欢喝早上的井水。因为一过了早上,奶奶家来的人多了,井水就显得没那么干净了。
到了半上午时节,附近从农田里干完农活上来的人,会到奶奶家天屋坐一坐、吹过堂风。一般是叫一声“婶几”,算是打招呼,然后就把手叉在水缸旁的墙壁边,支撑着身体舀一筒水,就着筒勺就喝。大约那时乡里人觉得水金贵,水没喝完,也没见倒出去,筒勺也没有洗,喝完就甩进了水缸。
听到来人了,后院的奶奶闻声出来,要么用井水泡甜酒糟,要么用井水泡粳米,要留一阵客。来人看着天屋里玩的我,不熟悉的,会上下打量着问:“这是哪来的客啊?”
小时候的夏天,奶奶家的客特别多。除了农忙时节的过路客,爷爷生日好像也是在夏天。七月半供老客也是夏天。
大多数时候,我回爷爷奶奶家时,已是“双抢”的尾声。到了半上午时节,太阳毒了,忙着零散农活的乡里人陆续回家,有的就在爷爷奶奶家四门敞开的天屋里坐着拉家常。二姑父一挨着躺椅就睡着了,脚上的泥巴还未清洗干净。
有的远亲世交的,要留人吃饭。老外婆那时,手还不抖,她拿着剪刀在剪辣椒,剪了一簸箕还不够,估摸着吃饭的人数,还要再剪一大碗。“老外外,我也要剪。”我抢着老外婆的剪刀。“辣!哎呦,哎呦……”老外婆装作被辣到的样子,我迟疑地撒掉抓在手里的那把辣椒,老外婆趁势叫我“好崽,快去洗手、快去洗手”。
待到晌午饭上桌,会有一碗红干辣椒炒田螺或者石螺。弟弟会和姑父去后院枣树上取一把枣树刺,好用来剔田螺肉。饭石(河蚌)、小鱼,都是水田渠道、池塘里捞的。丝瓜、豆角、茄子、苦瓜、小南瓜、小白菜、兰包是村口奶奶菜园子里现摘的。奶奶园子里还种了两蔸百合,怕人发现弄了去,奶奶每年把它们种在园子不起眼的地方,现吃现挖。夏天正是出百合的时候,奶奶习惯吃一蔸,再留一蔸给我们带去城里。百合肉片汤,在当时的乡间算是奶奶家饭桌上的一味稀罕物。就这样,主客随意,吃着夏天里的家常便饭。
再不成,就得杀鸡了。但那得到爷爷过生以及七月半去。就像刚回爷爷奶奶家那段时间,奶奶隔几天杀一只鸡给我和弟弟吃鸡腿一样。杀鸡及鸡腿的分配,是乡村的礼数。
爷爷过生到七月半之间,我们要先把后院的枣子打下来。这4棵枣树,两棵有三四层楼高,长在奶奶后院围墙根外,枣子掉下来,射程可以到围墙对面的人家去。另外两棵,就种在后院那片橘子树前面。
打枣子要等天刚蒙蒙亮,而且还得全家出动,米箩、簸箕、大兰盘(直径一两米的圆簸箕)都得用上。姑姑、姑父、叔叔,包括表弟大了以后,都参加过这样的“行动”。凌晨,后院屋廊下的灯亮着,爷爷拿着最粗最长的竹篙,“扑棱——扑棱”地往枣树尖上扑。枣子像雨点一样砸在我们身上,落在箩筐、簸箕里,打在地上、掉到沟里,我们先尽大个的果子捡。外面的两棵树还没打完捡完,天就全白了。
打完枣子,爷爷奶奶家就会来客人了。对面村的小爷爷,耒阳的表叔叔,荫田的表叔叔,还有爷爷以前工作的老同事,爷爷和外婆家共同的亲戚都会来给爷爷庆生。
荫田表叔叔来了的话,他的亲生母亲——爷爷早逝的妹妹的事情就会在客人都走完后被提起。我突然某一年才知道,那个将嚎啕大哭的我从村口的字库塔上抱下来的姑奶奶原来不是我的亲姑奶奶。有一年夏天,奶奶带我走过一个又一个村落,到了可以望见耒河的地方。那里的风物与奶奶村里的不同,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有枣树,沿河更是一排排果实累累的枣树,我再一次想起了那个从未谋面的姑奶奶。我小声问奶奶,我的亲姑奶奶是在这样的枣树上、摘这样的枣子,没了吗?“喉喽!”奶奶叹息般地应着,岔开我的问话,但又喃喃道:“那时大妹几都还好小。”走着走着,奶奶一边跟不知隐在哪里的人打招呼:“你看你屋今年咯枣子,怕是收得好几担。”
到了七月半供老客时,爷爷奶奶家里的客人,我就不全认识了。我们这个自然村只有五户人家,但却是附近何姓一族的发源地,所以叫何家老湾。我能认得的就是住在村里的太太们、小爷爷小奶奶们。供饭是轮流的,一般有几桌。来的都是客,我认不全客人,就只能笑。笑一下,就溜到门外柚子树下那一个饭桌前去坐着。
爷爷拿着香在四处找东西,见他经过我们这一桌,我大声问爷爷,“爷爷爷爷,为什么外面还摆一桌?”爷爷跺跺脚,觉得我不合时宜地淘气,但还是回答我道:“供老爷爷老奶奶啊。新打的粮食,要给老祖宗先吃啊。”“那这么点米饭,他们吃得饱吗?”我看看四方桌上8个小碗里一口口米饭,继续不解地问。爷爷跟我一时扯不清,就进了天屋。坐在对面的一个比我小好几岁的小爷爷嘻嘻地笑我,“摆在外面的是给夭亡的吃的。”见我不解,他又嘻嘻地告诉我,“你老爷爷第一个老婆还没生小孩子就死了。你不知道吧?”“你怎么知道?”“大人会说嘛。”“那我老爷爷呢?”小爷爷跟另一个小孩商量后认真地告诉我,“你老爷爷活了八十多,可以坐屋里面。”
于是我好几年暑假回爷爷奶奶家,都怕过七月半。奶奶家二楼厅堂摆着三具老屋墙,此时更让我困扰。奶奶说,这都是给老外婆以及他们自己备下的,哪一年哪一年又刷了遍桐油,“不要怕,里面没有人。有,也是自己亲人。”
爷爷一直嫌院子里两个枣树挡了橘子树的阳光。橘子树是妈妈怀我那年从她工作的地方带过来种下的,跟我一般大。而枣子树,却是老爷爷手里就种下的。爷爷终归是念旧,说归说,一时没有下决心砍枣树。不知哪一年,爷爷突然就把院子里面的两棵枣树砍掉了。后来,连橘子树爷爷也砍掉了,说是年月久了,味道变了,留着怕人惦记,反倒惹事。最后一次打枣子,我女儿已经有5岁了。如果没有记错,是爷爷80岁生日那年。
爷爷是八十多岁走的。爷爷走后,奶奶的生日,成为我们回老家的理由。奶奶的生日也是在夏天,我因为家事、工作,不如爸爸姑姑姑父们回得勤。我最终更像是老家的一个客人了。
有一日,奶奶在屋里听见枣树响得厉害,觉得一个老人单独住在院子里不安全,于是把院子外围墙那两棵最高的枣子树也砍掉了。
你知道我们当地收着枣子作什么用吗?许多人家把自家收的枣子晒干了,留着过年挂红用。像我的爷爷奶奶,会被儿孙们团团围坐,然后从果盘取两颗红枣放在每个儿孙面前的米酒里,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扯着喉咙,像开大会一样说着子孙绵长的祝福语。可如今没有枣树了怎么办?那就跟其他人家一样,去市场上买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