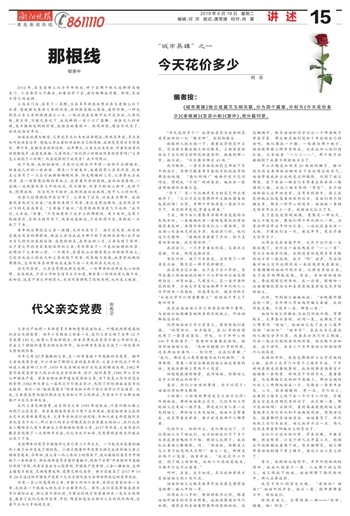编者按:
《城市英雄》独立成篇又互相关联,分为四个篇章,分别为《今天花价多少》《老板娘》《友谊小船》《窗外》,现分篇刊登。
“今天花价多少?”我将我在花店后面的花房里挑好的一打“戴安娜”,放到收银台。
收银的人把头抬一下,看看我拿的是什么花,然后低头翻台面上的记账本,上面密密麻麻记了当天到店的鲜花的进货价。她查到那一页,抬头说:“今天戴安娜是45块。”
我付账时,一旁正在插花的花艺师放下手中的活计,用那只戴着布手套的手抓住我买的那束粉玫瑰。“要打刺吗?”她动手前不忘问问我。得到我“不用”的回答后,她扯出一张透明玻璃纸准备打包。
“等下。”另一个比她年长点的花艺师示意她停下,“上次不是还有那种外文报纸图案的包装纸吗?去拿,用那个外面再包一层就不扎手了。而且配单色花,拿着也好看。”
于是,两个女人窸窸窣窣拆开原包装的白色吸水纸,一层玻璃纸再一层硬包装纸地将玫瑰花束包好,再随手给花束扎上一根麻绳,然后满心欢喜地交到我手里。我临出门时,他们还不忘嘱咐:“玻璃纸里面蓄了点水,你不急着回家的话,还足够保鲜。”
我退出门,一只手拿着我的花,笑着点头感谢,然后,慢慢走路回家。
等红灯时,换了只手拎花,突然有了一种身在云南、像买菜一样买花的错觉。
我没有去过云南。我只在十五六岁时,曾听我最小的姑姑说过她十六七岁时对云南昆明的向往:四季如春,气候宜人,是一座开满鲜花的城市。云南大学是姑姑她那个年代的人心目中的双一流高校。但高考失利,被老师料定“云南大学可以闭着眼睛上”的姑姑只考上了衡阳师专。
我是在姑姑姑父乔迁新居后的那个暑假,与姑姑打地铺睡在她新房的木地板上,听姑姑聊起这些的。
记得姑姑姑父乔迁家宴上,爸爸给他们敬酒:“祝贺你们,白手起家,在30岁的时候就有了一套靠近医院、学校,位于市中心的100平米的房子。”爸爸回头看看我妈妈,继续对姑姑姑父说:“我和你嫂嫂30岁的时候,还在两地分居吧……你们啊,比我们要强。”“我们,都还是以哥哥嫂嫂为我们的榜样。”文质彬彬、驾着一副金边眼镜的姑父接过爸爸的话,笑起来脸颊上有两个小窝窝。
回想起敬酒的场景,我问姑姑,你跟姑父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呀?
莫非,你们小时候的事情,你不记得了?姑姑惊讶地睁大眼睛。
小时候?小时候的事情我怎么会不记得?听妈妈说,那时姑姑要去实习,已经参加工作的姑父过来送一块手表,那是我们家人第一次见到姑父。那时姑父来见姑姑,姑姑不是带着我,就是带着我弟弟,要么就是把两个人都带着。
吃的什么、玩的什么,我们都忘记了。只记得姑父为了哄我们,也不知给我们买了多少米老鼠唐老鸭的不干贴。跟姑父玩熟了,我就扒拉着姑父眼睛瞧,问:“唐叔叔,你眼皮上怎么有个红色的点点啊?”姑父一笑,两颊笑出两个小窝窝,他告诉我:“我这是个小灯泡。到了晚上的时候,我的小灯泡就亮起来,不要开灯也可以看书。”
呵呵,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我和弟弟才是姑姑姑父的小电灯泡。
姑姑和姑父大概是改革开放后最先懂得浪漫的那一拨人中的一员。
记得我七八岁时,晴朗的秋冬之际,跟着姑姑外语系的同学去野餐,我把佐餐酒当作汽水喝,喝得歪倒在铺着野餐布的茶树林地。迷迷糊糊中,瞧见姑姑和同学们往一个啤酒瓶子里塞字条。那大概是他们写给十年后的自己的话吧。他们围成一个圈,一起握住那个瓶子,姑姑赶紧抱上醉熏熏的我,让我也加入他们的队伍。大家喊着“一二三——”,那个瓶子就被抛到了我看不到的地方去了。
中山北路走私街买20块钱的裙子、路口的冷饮店要两杯冰咖啡坐下来边喝边吹冷气,姑姑带着我出去走的是这种路线。而到了姑父那里,是下班后一辆自行车带着我和弟弟一路溜到三塘,去逛三塘老街的“冒险”。至于姑姑和姑父过年回老家,没有坐到班车,搭上农民的拖拉机晃荡着回家的经历,在他们两个的描述里,都是一种开心的经历。姑姑把一条挡灰的丝巾往头上一系,就被姑父拉上了车。
至于表达爱情的玫瑰,更像是一种仪式。姑父不能免俗,像他们那个年代的人一样,注重这种过年过节的仪式感,一送就是喜欢送一大把。不像我们这一代,看淡年节,更在乎每天花价多少。
记得我还在读高中时,突然不流行送一大把玫瑰了,流行送一朵玫瑰表示“一心一意”。有次去姑姑家吃饭,我刚进屋就发现家里显眼的地方有一枝玫瑰。我才“啊”出声,然后准备对姑父突然也跟风送一朵玫瑰要发表看法,系着围裙的姑姑听到声音,从厨房里钻出来,先于我拿到那枝玫瑰,然后,再炫耀地递给我,要我闻闻它的香味。我一边闻,眼睛却一边滴溜溜地望向正和表弟在饭桌前临毛笔字帖的姑父。
此时,听到姑父幽幽地说:“如晚报所报道的一样,今年情人节玫瑰价格太离谱。我的荷包太瘪,只能买一朵,聊表心意。”
姑姑与姑父结婚后,与我们同城而居,有事联系,无事各忙各的。时间一晃,我都成了别人嘴里的“姑姑”,姑姑姑父成了我女儿最年轻的“姑奶奶”“姑爷爷”。在我与自己喜欢的人微信分享位置,玩着在公共汽车上偶遇、然后一起去吃饭的游戏的时候,他大概不会知道,这个游戏,来自二十多年前姑父和姑姑两个人的创意。
我读初中时,住在先锋路职工大学对面的6楼。在职工大学门口有个2路车车站。下午妈妈在厨房准备晚餐时,我会到厨房隔着窗户玻璃看一会街景。特别是干冷的冬天,看着看着,与先锋路交叉的和平南路上,那些店铺的灯就三三两两地融成一片,勾勒出一条夜市出来。心头,就会暖暖的。有一次,华灯初上,我看到2路车上跳下来一个个子小巧的、穿藏蓝太空夹克的烟花烫的女子。我定睛一看,那不是姑姑吗?正纳闷,看到高高瘦瘦的姑父骑着辆男式自行车从和平南路慢慢游,慢慢游过来,掂着脚停在姑姑身边。姑姑看见了,麻利地跳上自行车后座。姑父把车头正一正,两人就径直朝着衡阳城边上的家去了。
这如行云流水的日常,节奏准确,步骤清晰,配合默契。以至于好几次早晨6点,妈妈也开始提醒我看楼下说,你还睡懒觉,姑父都带着姑姑到楼下等2路车,要过江去江东上班了。
有次,我刚好也起得早,耳中听到妈妈的唠叨,我就趴到窗户一看。人迹稀少的大街上,姑父刚放下姑姑,姑姑刚解下挡风的丝巾,两人正要道别。
我忍不住趴到窗台大喊:“唐叔叔!姑姑!”姑姑听到声音,抬头一看,随即挥舞着头巾,朝向我们。
特别是姑父,长臂轻轻一挥——“你好,嫂嫂。嗨!何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