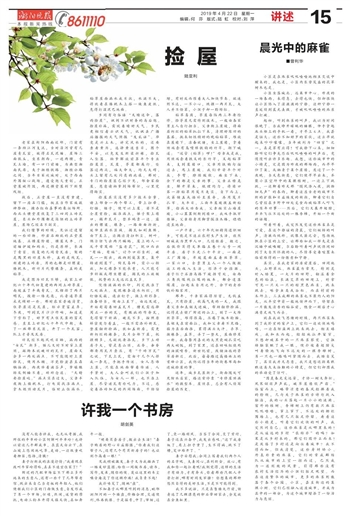老家在衡阳西南近郊,门前有一条柿江河支流,古时沿河曾有几座青瓦窑,故得名瓦泥塘。屋场三面低丘,坐东朝西,一进两横,青瓦土墙,有一口门前塘,为典型湘南民居,夹于湘桂铁路、湘桂公路之间。当年日军攻城时,处于西南外围核心战场,遭受炮火重创,正堂屋被炸毁,两进横堂屋剩下断壁残垣。
战后,正堂屋一直没有重建,留下一座石门槛,权且当作家族敬神祭祖、操办红白喜事的象征场所。西北头横堂屋恢复了三四间土砖瓦屋,东头和外围都是简陋的土砖茅屋,屋场已经名不副实。
我们懂事的时候,见证过遗留的一些旧物。砂岩石砌就的正堂屋地基、正横屋阶檐、横屋天井、门前塘护坡和码头,仍是原样,长满了青苔。恢复的几间青瓦房,架的是黢黑的旧屋木料,盖的是残瓦。新建的土砖房,用的也都是旧檩梁、楼枕木,新竹片代替椽条,盖的是稻草。
或是因为旧瓦不够,我家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复建的两间土砖茅屋,南坡盖了半截青瓦。瓦楞排了两片明瓦,投射一缕光亮,比普通茅屋采光稍好一些。那时农家普遍清贫,住茅屋还是瓦屋,标示贫富差异。冬夜,听到瓦片沙沙作响,知道是下雪粒了,好歹有点住瓦屋的富足感。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来了一班邵东瓦匠,开了一个瓦窑,队上才普及瓦房。
旧瓦经不起风吹日晒,漏雨的“女瓦”渐多。猫儿又时不时窜上屋顶,踩踏本就破旧的瓦片,屋面又会多一两处漏点。不可能随时上屋捡瓦,便用木桶、洋瓷脸盆甚至鼎锅接漏。雨夜伴着滴答声,爹娘辗转反侧睡不着,碎碎念道:“天晴要捡屋哒。”漏点实在过大,父亲半夜爬上楼枕木,打电筒找准漏点,拿木棍顶动瓦片,临时止住漏水。稻草屋面漏水成片状,水滴不大,将就着在楼枕木上搭一块鱼皮纸,免得打湿泥巴地面。
乡间有句俗语“天晴送伞,落雨捡屋”,讽刺不识时务的马后炮。捡屋补漏,需就着晴好天气。乡民更相信看云识天气,讥讽县广播站播报的天气预报“发乱话”。毕竟是兴土木,讲究风水的,还要查看黄历,选择黄道吉日,图个平安,以免发生断梁折椽,捡瓦人坠落。柏爹解放前算半个专业捡屋匠,瓦屋、茅屋都属行。坠落过两次,福大命大,均无大碍,头上留有几处闪亮的疤痕。那时,专门的捡屋匠已经少见,邻舍家捡屋,愿意请柏爹到场帮忙,心里觉得踏实。
捡屋其实没有多少技术含量,请上邻舍一两个帮工,带上扫帚、钉锤、锯子,便可以上屋。若不是全屋重捡,踩准漏点,梯子架上檐口,揭开瓦片,整齐码靠一边。露出的檩梁、椽条,一路曲曲折折,延伸至漏水区域。揭瓦如刮鱼鳞,由下至上,边揭边清扫积尘、树叶。偶尔惊飞出两只蝙蝠,屋上的人一反平常蔑称“盐老鼠”,脱口而出“有福,有福”,讨个口彩吉利。破瓦一一剔出,收纳到箢箕里,集中转递到屋下。陶瓦易碎,需小心轻放,加之椽条不能承重,人只能弓步斜踩或蹲坐檩梁,揭瓦的工效极低,耗费的工夫远比盖瓦多。
凭借滴漏的水印,判定找准了几处漏点。发现椽条浸水朽烂,用钉锤反敲,退出钉子,换上新杉条。准备停当,便由上至下、由远及近,开始匍匐着回盖瓦片。槽瓦需选择周正一些的瓦,有瑕疵的作脊瓦,免得留下新漏。破瓦不多,按照原样密度匀着盖,一般不需添补新瓦。整屋翻新捡漏,犹如盖新房,需更新朽烂的椽条,瓦片全部下屋,耗损稍多,无疑就要添瓦。乡下土砖房子大,皆是悬山顶,正脊、垂脊都要用瓦片叠压,有“千砖万瓦”之说。下瓦上瓦,需由十几个人排成一条龙,手把手传送。女人忌讳上屋,只能在地面帮着传递。人手紧时,大人会叫我们小孩子加入队伍,与女人一样,也不准上屋。尽管递瓦有些吃力,不过,感受着添砖加瓦的热闹场面,干劲倍增,有时反而催着大人加快节奏。欲速则不达,一不小心,跌损一两片瓦,大人并不怪罪,小孩子却一脸绯红。
稻草易腐,茅屋每隔两三年要检修。捡茅屋无需特别技术,一般由各家男主人自行担当。父亲爬上屋坡,将面层朽烂的稻草扒拉下来,清理好陈旧的基层。挑来韧性稍好的晚稻稻草,堆放在屋檐下。准备就绪,坐上屋檐,拿着顶端套有鸟嘴样铁钩的竹竿,朝下喊道:“送管(稻草)啰!”母亲或是我,用顶端套着铁叉的长竹竿,叉起稻草束,支到屋檐口。父亲用铁钩勾接过去,甩上屋坡。我们辛苦半个时辰,手臂、脖颈酸软,瘫坐下来,余下的都是父亲的事。父亲正襟危坐,解开草束,梳理均匀,将檐口第一排稻草用篾片夹实。自下而上,次第铺盖或插补至屋脊,再用篾片扎牢。大半日,三面半屋坡披盖新稻草,捡漏大功告成。父亲踩实山墙屋坡,小心翼翼倒爬到檐口。我双手抵牢楼梯,父亲转身用脚掌探准木格,稳稳退至地面。
一户干亲,六十年代初精简退职回乡,可能是不适应农村生产生活,毅然回城成为黑市人口。几经租房、搬迁,后低价买得文革路五巷十七号一间平房。房子不足二十平方,一面是工厂围墙,单坡屋面盖着丝茅草。一家六口,全靠男主人一个人做搬运工的收入生活,经济十分拮据。房子位于石渣马路下坡拐弯处,由西三角线煤栈拉煤的板车,都会遗落煤屑,扫起来自用之外,余下的卖些钱补贴家用。
那年,干亲家漏得厉害,无钱盖瓦,只有捡屋。秋高气爽的一天,我跟着父亲和表姐夫进城,帮助翻修捡漏。记得是去锁厂附近的山上,割了一大堆丝茅草,堆得很高,压瘪了板车轮胎。表姐夫在前面拉,我和父亲看不见路,猛力在后面推,累得满头大汗。杀草、换椽条、盖草,弄了一整天,屋面修葺一新。我每餐用喜欢的大黑瓷碗扎实吃两大碗饭,到了家里,还在回味红烧肉的油腻喷香。新世纪前,改铺油毡的茅草房拆迁。此后,每每路过高楼林立的首峰小区,我仍记得当年的街巷布局和进城捡屋的事。
近年,城乡瓦屋渐少,街面随处可见防水店家,路边常停靠“专修屋顶漏水”的微型车。屋顶在,总会有人续写捡屋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