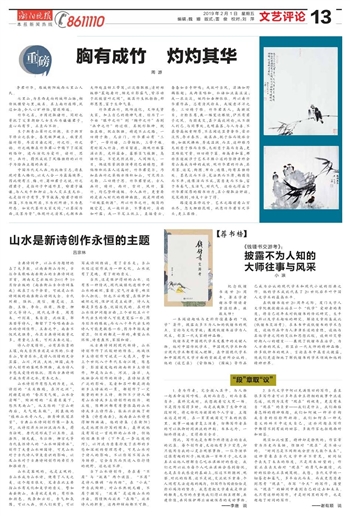古典诗词中,以山水为题材的占了大多数。以南岳衡山为例,古往今来歌咏南岳衡山的古典诗词近万首,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10月份出版的《南岳衡山古今诗词集成》收录了七千余首,可说是山水诗词版的南岳衡山诗词大全。古代刘桢、陆机、庾信、谢灵运、王勃、王维、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诗人,现代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朱自清、沈祖棻、郭沫若等诗人,都留下了吟唱南岳山水的诗词佳作。五岳之中,南岳不仅风光独秀,而且古典诗词数量之多,质量之上乘,可列五岳之冠。
诗人抒发情怀,必有其依靠的土壤,向大自然亲近是必然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是诗人性情的充分显露。山川、河流、大地、田园,成为诗人创作的客观参照物,成为诗人乡愁或爱情的依托。因而古典诗词才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山水诗创作有悠久的历史,从诗经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到谢灵运的“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王维的“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到袁枚的“桂林山水奇八九,独秀峰犹冠其首”,古典山水诗词创作像一条大河,从诗经源头汩汩流淌而来,蔚为壮观。唐代还形成了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韦应物、柳宗元等为代表性诗人的“山水田园诗派”,创作了大量山水田园诗。可见山水对于古代诗人审美意识的影响,以及山水对于古典诗词创作的牵引力和推动力。
山水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当山水成为山水诗,便有了人文之美。这个题目很大。笔者在此主要指山水有文化和美学的意义。譬如南岳衡山,本身就是美的,有形体和颜色,线条和云彩,香气和氛围,可以入画,供人们欣赏;可以写成诗词朗诵,有了音乐美;当山水经过创作成为一种文化,山水就有了灵魂,有了新的意义。
当然,这是保护得好的山水。还有另一种情况,现代城镇化进程中对山水的破坏,雾霾、空气污染等,确实令人担忧。但也不必绝望,在保护和破坏之间,保护还是主旋律。诗人大都是多愁善感、忧国忧民的。在对待山水保护问题方面,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可能更宽容一些,因为经历的缘故;而七八十年代出生的诗人可能更敏感一些,因为年轻或者前卫。但目的都是一样的,希望山水环保,诗意盎然,家园和谐。
从古典诗词到现代新诗,山水诗创作作了比较好的传承。地域性乡土诗创作可说是一大亮点,譬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由江堤、陈惠芳、彭国梁发起的湖南新乡土诗创作,即是与山水、河流、海洋、大地融合而创作的新诗,在诗坛具有广泛的影响。笔者和吕叶都是湖南新乡土诗派的一员,都创作了一定数量的新乡土诗。衡阳不少诗人都有山水诗或乡土诗创作的经历。胡丘陵、陈群洲都有质量很高的山水诗或乡土诗作品;张沐兴出版了新诗集《诗意南岳》,把南岳山水诗意得酣畅淋漓,他的诗集《在衡阳》也是地理性抒写的模本;聂沛说他没有写过一首纯粹的山水诗,但他的经典长诗《下午是一条远逝的河》,以河流为意象抒发了浓郁的乡愁和深刻的哲理思考,可见山水对于诗人的影响,不以你写不写山水为转移,它会自然而然进入你抒情的视野,逃也逃不掉。
当下山水诗创作,存在着“不屑”与“疏离”两个误区。“不屑”是诗人强调“向内转”,在“小我”中自我陶醉,对山水熟视无睹,不屑于描写;“疏离”是逃避山水的汚染,因愤慨而放弃“在场”,放弃诗人的职责。这两种倾向都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