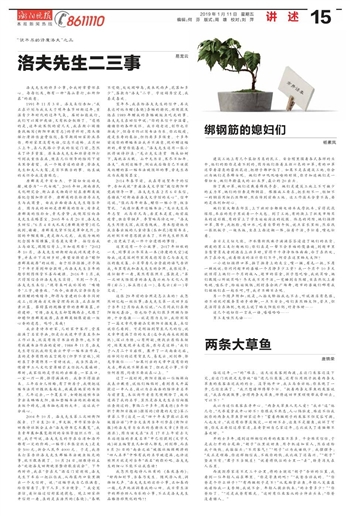洛夫先生的许多小事,令我时常萦怀在心。每每忆及,都有一种“高山景行,私所仰慕”的敬意。
1991年11月3日,洛夫来信告知:“我正在计划与我太太于明年春节回衡过年,重温青少年时代的过年气氛,届时如能成行,我们可以围炉夜话,又有机会叙晤了。”遗憾的是,这年放寒假的前几天,我在爬小阁楼查找编写《衡阳市教育志》的资料时,因木楼梯打滑摔伤盆骨住院,春节期间回家卧床养伤。那时家里没有电话,信息不通畅。正月初三上午,在人民路小学我的住宅门前,忽然来了许多贵客。原来洛夫先生和琼芳老师打听到我重伤在床,便在几位领导的陪同下前来寒舍看望。我一个极普通的读者,劳洛夫先生和夫人大驾,是实不敢当的事。他至诚的关怀令我没齿难忘。
唐群英是辛亥女杰、中国妇女运动先驱,被誉为“一代女魂”。2005年初,湖南唐氏文化研究会、衡山县文物局计划在唐群英故居纪念园加修凉亭。唐群英的长孙唐存正先生与我商量,由我出面请洛夫先生题签亭名。因为我的奶奶是唐群英的侄女,母亲是唐群英的侄孙女,责无旁贷,我便写信向洛夫先生求赐墨宝。2005年6月20日,洛夫先生回信:“6月4日大札及《唐群英诗赞》近已收到,谢谢。唐群英先贤不仅是革命先烈,全国的巾帼英雄,更是湘人之光。我能为她的纪念园书写横匾,实感莫大荣幸。接信后我立马动笔,现随信寄上,不知适用否?”2012年10月,洛夫先生回衡时向我问及建亭之事,并表示下次回乡时,希望安排前去“瞻仰唐群英故居”的议程。由于经济拮据,凉亭拖了十年才筹到部分款项,而洛夫先生当年的题字则因保管不善而破损。2016年1月,我只得写信告诉洛夫先生实情。不到一个月,洛夫先生来信:“现寄来叫我补写的‘唤晴亭’三字,请查收。”而今,由唐氏宗亲仕亮全额捐赠的唤晴亭,即将与重建的仁寿亭同时竣工;经湖南省文物管理局批准,正在按照黄兴墓、蔡锷墓的规格重修的唐群英墓,亦将建好。可惜,洛夫先生却驾鹤西去,无缘了却瞻仰唐群英故居,在唐群英铜像前敬一炷心香的遗愿。呜呼,哀哉!
我出身诗书世家,儿时家中客厅、堂屋挂满了名家字画,但是打我进中学直至参加工作以来,就没有练习书法的条件,也不曾有收藏书法作品的爱好。1988年11月,洛夫先生寄信托我转交岳云中学一幅书法作品,录的是李商隐的五言绝句《归梦不宜秋》,同时录了李商隐另一首诗送我。我当然高兴,便请市工人文化宫蒋昭芒主任托人装裱好。那时,我家住的是学校的出租房,一家五口,一室一厅一厨,挤得满满的。我舍不得挂出来。三年后女儿结婚,有了新房子,我便把这幅书法用旧报纸卷起来,收藏在她家的书柜里。几年过去,一个夏至日,女婿把这帧书法拿出来晒晒太阳,谁知整幅书法的纸面被蛀虫蛀个精光,连书轴也腐朽大半。这让我十分痛心。
2004年10月,洛夫先生第三次回衡阳探亲。17日至20日,市文联、市作家协会与回雁诗社联合主办“洛夫诗书艺术展览”,我负责布展和展览期间的安保等组织工作。这时,我才听说,洛夫先生的字在台湾和海外都有一定的价码,一幅字(半张宣纸大)是美金500元,折合人民币4000元。于是,我原来打算告诉洛夫先生那幅书法被虫蛀光的事,就不敢再提了。10月24日,迴雁诗社主办“欢迎洛夫回衡晚宴暨诗歌座谈会”。下午两时许,我在“食在天”酒店门前迎候,洛夫先生下车后一把拉住我,从西装内口袋里掏出一个大信封,说:“这幅字我自己很满意,给你留着了,等下人多,不方便拿。” 我受宠若惊,连忙接过信封装进提包。晚上回家拆开信封一看,录的是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落款为“洛夫”二字。字迹娟秀空灵,我甚是喜欢。
翌年冬,我在给洛夫先生的信中,再次表达对他书赠《春晓》条幅的谢忱,顺便提及他在1989年赠我的条幅被蛀虫吃光的事。洛夫先生在回信中说:“你的来信十分温馨,谢谢你的各种关怀。我日趋老迈,创作也日渐减少,但每日仍以写书法为乐。你比较瘦,瘦是长寿的象征,但仍要多多保重。十多年前送你的那幅书法我并不满意,现补赠这幅新的,希望你能喜欢。”洛夫先生还用一张小纸将该诗抄录:“龙云先生清赏 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洛夫”。收到这幅字,倒让我后悔自己不该提及他赠的第一幅书法被毁坏的事,劳先生再次为我题写墨宝。
2014年春节前,我在寄送贺年卡的信中,告知我就“重启洛夫文学馆”致信衡阳市党政领导一事。洛夫先生在2月6日来信,感谢我“对衡南县洛夫文学馆的关心”。信中还说,“值此马年新春,赠你一幅小字,权当贺礼。”我连忙展开这幅书法:“龙云先生马年志贺 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独自带铜声。李贺咏马诗之四。”洛夫先生用情太深,我深感愧疚。原本想请他为我准备出版的儿童诗集《瓜和花》题写书名,此时倒不好意思提出来了。不料先生猝然离世,这竟成了我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
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2017年初秋的一天,同事肖江华买来一本《诗魔的天空》送给我,这是深圳作家周友德写自己与洛夫交往的散文集。小肖带着几分崇敬的语气告诉我,书里有我和洛夫先生的合照。我很诧异,连忙翻开一看,果然有张照片,落款是:“第一次回大陆探亲的洛夫高兴地与文化人蒋薛(右二)、谷五德(左一)、易龙云(右一)等交谈。”
这张29年前的合照是怎么来的?我忽然回忆起一桩往事:洛夫先生第一次回乡后于当年12月给我来信说:“八月间我们在衡阳相处甚洽,你也给予我们很多照顾与协助,十分感激……就是因为太忙,我特别写了一篇文章代替谢函交衡阳日报发表,来信说你已看到。可是刚接到贺良凡兄的信,说文章中遗漏了你的大名(迄今我尚未收到报纸),深以为怪,心有所疑,便找出原稿来核对,结果发现并未遗漏,原句是这样:‘我们于八月二十日启程,展开了一次南岳之旅,结伴同行的还有贺良凡、易龙云、刘剑桦、郭龙等数位……’如果刊出的文章中没有你的大名,那我就不解其故了。但此是小事,不管任何原因,均请不要放在心上。”
过了一段时间,衡阳日报社一位编辑向我表示歉意,说他们编稿时,看到原文开篇提过一串人名,误以为去南岳的陪伴者名单与前重复,未征询作者意见便删除了,故而遗漏了我的名字。显然是洛夫先生去信向报社查询过的。事隔二十多年,周友德(当年任职于衡阳日报社)撰写的《诗魔的天空》第二章第三节《这是一次“四十年来梦寐以求的故园壮游”》中全文录用当年刊登在《衡阳日报》的洛夫寄自台北的感谢性文章《乡情比酒浓》,因为该文在“8月17日上午前去火车站迎接的亲友名单”中已经提到《文学天地》副主编贺良凡和诗人郭龙、刘剑桦,而在8月20日的“南岳之旅”被报社编辑删掉的“四人名单”中唯有我的名字被遗漏,也许这帧照片就是对当年“漏名”的弥补吧。洛夫先生的细心不能不让我感动!
我忽然想起诗人杜甫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洛夫先生的这些小事,正如春雨一般,无声地滋润着我的心田。我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助人为乐的小事,不正是洛夫先生品格潜移默化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