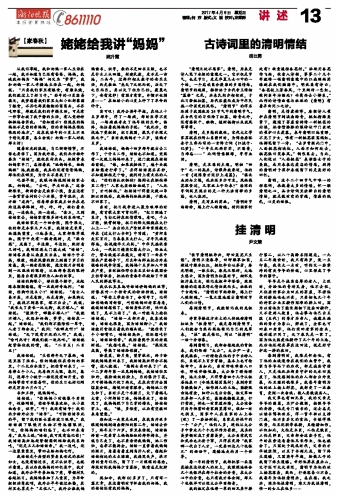“佳节清明桃李兴,野田荒芜只生愁”。清明正逢春季,田野绿草如茵,嫩枝叶绿水汪汪,桃红李白吐芬芳,春光明媚,一派生机。春光无限好,大地生愁云,因为清明为扫墓时节,缅怀先祖开基立业,惦记先祖辛辛苦苦,丝丝缕缕的追思哀悼之情油然而生。杜牧的千古绝唱:“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一览无遗地道出清明时节人们的心情。
每到清明节,我就惦记我的先祖来。
许家吊楼这方水土的人传统称清明扫坟为“挂清明”,就是每到清明节,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惦记自己的先辈来,“挂”就是惦记,所以“挂清明”一语十分形象。
每到清明日,我都会想起我的曾祖来,我们俗称“太公”。太公尹一吉,尚武疏农,一杆猎枪在他的手中出神入化,虽说不上百步穿杨,基本上也可枪枪命中。虽如此,当时野味难诱人口味,野味价格低廉。太公除了猎枪猎狗,地无立锥,只得带着四个儿子从祖居地泉口(今鸡笼镇团集村)来到许家吊楼做佃户,佃作别人的土地。勤耕陇亩地有金,细种山皂出白银,祖父辈四兄弟都一人多艺,蒸酒熬糖做豆腐,行行营运,倒也一时家道兴隆,太公准备用历年积蓄回老家购置薄田。谁知一时之祸至,因家中人在东家的山上体(砍)了一些松树枝,东家是许姓中的一个“公产,”他们人多,硬性从太公手中拿走几十个光洋作为罚款,成真的美梦顿时成了黄粱美梦,太公虽有武艺和武功也无济于事,只得在交待“我家哪一代出了人才,一定要回这几十块银元”的话语中,遗憾地走向另一个世界。
每一年的清明节,我都把第一朵奠花插在这位老人的坟上,我深深地体会几十块银洋在那个社会的分量,在太公心中的分量,也只有我才体会到,那几十块银洋可以使太公华丽转身。
我的祖父在他那一辈的四兄弟中排行第二,以八十高龄名闻遐迩。一九五二年逝世时,我只有两岁,没一点印象,我长大一点时,听伯父一些零碎的有关爷爷的传说,心里形成了爷爷的影子。
爷爷是个诚实忠厚的老人,土改时,分给他的青砖瓦房,他不去住,只住原许家公业田庄的茅屋,旱涝保收的耕地他也不要,只要佃包几十年的许家公业且耕作困难的排上田。因为以前他为了能长期佃下这些田耕种,又不受别人欺负,他去攀与他已出五服(五代)的秀才为亲人,诚邀本族姓的秀才为靠山,解放了,全家也可回泉口老家,他打消回老家的念头,说世道不同了,天下农民是一家了。因为他太热爱他耕种了几十年的土地,死后他还硬要葬在这田边,说是好守护这一排的农田。
每到清明时,我很是怀念他。有了他的血液遗传在我们的血管中,我家自爷爷而下的后代,都是诚实守信人,只是他死后都要守护的天水田荒废了,他没想到他的后人都会出外发展,而且赚的钱很多。我每年清明为他的坟上插上鲜花,我都受了一次教育,受到一次告诫:做人要做诚实人。
我父辈也有四兄弟,我的父亲是爷爷的满崽。名尹公毅朝,按照爷爷的安排,他是专门读书的,过去总是以读书博取功名,得一官半职以支撑门庭,他不负其父的重托,书读得很优秀,而且还剽学农耕,且精耕细作。不仅如此,大伯是木匠,二伯是铁匠,三伯是弹匠,父亲都会这些手艺,他平时在旁边看着他兄长作业,他也就会了。只因处于战乱时代,父亲的才华被湮埋,以至于书剑无成,留下终生遗憾,又因英年早逝,给做儿子的我留下终生遗憾。幸好他葬在屋后山,父子还可天天亲近,清明节为他的坟上插花容易,然而,行动容易心不易。我每年为他挂清明后,总在想:我之后,谁为他挂清明,谁又为我挂清明,惟一的女儿在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