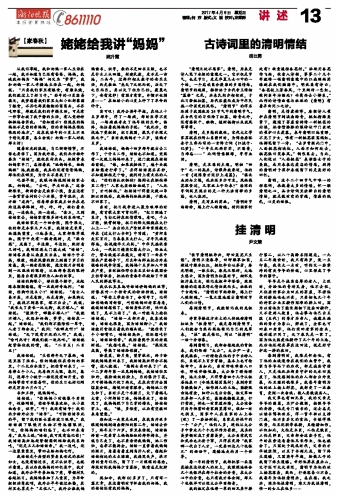姚升霞
从我记事起,我和奶妈一家人生活在一起,我不知道自己还有爸爸、妈妈。我喊我奶妈为“妈妈”奶父为“爹爹”,我和奶妈一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奶妈说:“只要我们家里有粮食,有柴禾烧,我们就过上了好日子。”幼年的心灵容易满足,我梦想着我们家里大缸小缸都装满了粮食,不再吃那黑糊糊的窝窝头,不再吃野菜,那就是我们的幸福生活。可是有一件事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有人竟神神秘秘地告诉我:“你知道不?你现在的妈妈她不是你的亲妈妈,你的亲妈妈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这在我幼年的心灵上不亚于晴天霹雳,怎么会呢?奶妈一家人对我那么好!
随着时光的流逝,自己渐渐懂事,不信也要信了。因为我外婆,我们北方称外婆为“姥姥”,就住在村北头。她经常来奶妈家串门,总指着我“她妈妈长,她妈妈短”地,我就想,我真的还有爸爸妈妈,那他们在哪里,为什么不要我了?
吃罢早饭,我跟奶妈说到姥姥家去玩。奶妈说:“去吧,早点回来。”这条街很长,街两旁全是农家小院,靠左边有一条贯穿全村的小小水渠,常年流水,北方称“龙沟”。你看那些家庭主妇坐在龙沟边高举棒槌,砰、砰、砰,槌打着衣服,一边洗衣,还一边说:“金玉,又到姥姥家去,姥姥家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哩。”
我姥姥家是一个四合院,院子很大,住的都是本家几户人家。我姥姥是长辈,她德高望重,心地善良,大家都很尊敬她。院子中央有一棵老梨树,是“秋白梨”,成熟了,半边绿,半边红,既好看又好吃。我刚迈进大门就大喊“姥姥”,姥姥答应着从南屋里出来。姥姥个子不高,很瘦,饱受风霜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沧桑。戴一副老花眼镜,透过镜片分明看到一双混浊的眼睛,从她那昏花的眼神里,能看出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姥姥的脚很小,形状像个粽子,走起路来颤颤悠悠。有一次我好奇地问:“姥姥,你脚咋这么小?”姥姥说:“看女人美不美,不是看脸,而是看脚,如果脚大了,就找不到婆家,嫁不出去。”我说:“我长大了要长一双大脚,我不嫁人。”姥姥说:“傻孩子,哪能不嫁人?”“我就不嫁人,永远和奶妈、爹爹、姥姥在一起。”姥姥说:“我们都不能陪你一辈子,人老了都会走。”我问:“往哪走啊?”姥姥说:“天下没有不死的人啊。”我说:“啥叫死呀?那我们就一块死吧。”姥姥就赶紧捂住我的嘴,说:“二百五!二百五!”
我姥姥说:“生你那年天下暴雨,咱这里涨了洪水。你奶妈就住在你奶奶家里。十二天后水退了。把你背回来了,一看那么个小人。光看两只大眼,忽闪,忽闪,连那个小被子一称还没有四斤重。你奶妈带你可不容易啊。你的生日也好记刚好是阴历六月六日。”
书归正传,说妈妈吧。
姥姥说:“你妈妈小时候像个男孩子,性格刚强,你姥爷很喜欢她,从小教她念书,识字。”咋?我还有姥爷?我们北方称外公为“姥爷”。“可怜你姥爷死的早,留下我们孤女寡母渡日艰难。”我姥姥摘下眼镜用衣袖不停地擦眼泪,“哎,你妈妈把咱们忘了,也不回来看看。”我马上说:“姥姥,我可没有忘记你!”我姥姥高兴地赶紧翻箱倒柜给我找东西吃,“还是玉儿和姥姥亲。”我一边吃,还一边装袋袋里,带回去给奶妈吃啊。
我姥姥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式的农村妇女,也没有读过书,更不认识字,也说不清楚。在以后我妈妈的回忆录中,我才知道,我外公早年参加地下党,带领村民奋起抗日。我妈妈参加了儿童团,为革命组织站岗放哨,我外公早年读过私塾,在村里也算是个“文化人”,我外公教我妈妈读书、识字,教的不是四书五经,也不是什么三从四德,封建礼教,更不是一亩地,二头牛,过那种相夫教子的安乐生活,而是教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以天下任为己任。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有国才有家。巾帼不让须眉……”在她幼小的心灵上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实可叹!我外公英年早逝。在他三十五岁那年,得了一场病,那时医学不发达,一场痢疾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临终,他拉着我妈妈的手说:“我死后,你找地下党组织,抗日救国,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我妈妈才十三岁,姨妈才五岁。
我姥姥说,妈妈十四岁那年就出去工作了,干什么工作,姥姥也不知道。突然有一天晚上妈妈回来了,进门就跪在姥姥面前说:“娘,如果我牺牲了,磕个头就当给您老行孝了。”弄得姥姥莫名其妙,不知道牺牲是干啥,就问村上有文化的人说:“你们谁认识牺牲?俺闺女在牺牲那里工作?”人家也实话给她说了:“人死了,才叫牺牲。”把姥姥吓得整天提心吊胆以泪洗面。我妈妈怕她拖后腿,干脆也不回家了。
当时,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难的时期,有首歌大家可曾记得:“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铁臂铜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元帅在《过太行山书怀》中写道:“黄河东走汇百川,自耒表里太行山,万年民旅发祥地,抗战精华又此间。”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一代抗日精英汇聚太行山,浴血太行,誓与敌寇不共戴天,谱写了一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生命与鲜血抗击外来侵略的战争诗篇。我妈妈十五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担任邢台县五区妇女救国会主任等职务,把她的青春年华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我认认真真地听姥姥讲妈妈的故事,好像在听一个传奇式的神话传说。姥姥说:“等你上学念书了,会写字了,记得给你妈妈写封信,叫你妈妈回老家看看,就说姥姥想你了,姥姥身体不好,怕回来晚了,见不上面了。”我一听就马上抱住姥姥说:“姥姥一点都不老,我喜欢姥姥,姥姥也很美,因为姥姥脚小。”我姥姥就用食指点着我的额头说:“就你长了个小甜嘴巴,哄姥姥高兴,你还想吃什么,姥姥给你拿。”我指着院子里的老梨树说:“我想吃梨。”姥姥说:“梨还没成熟,等熟了姥姥给你摘。”
盼星星、盼月亮,望穿秋水,终于盼到我妈妈要回来了,我姥姥高兴得合不拢嘴,逢人就说:“俺闺女要回来了!”我十二岁那年第一次见到妈妈,我姥姥忙里忙外,满脸皱纹的脸上,乐的像开了花。只可惜妈妈只住了两天,是在北京开全国煤炭会议,顺便回老家探亲。妈妈她工作太忙了。当时正是十冬腊月,天下着鹅毛大雪,小河都结了冰。妈妈要走了,姥姥哭了,我妈妈脱下自己穿的棉衣,给姥姥穿上,说:“娘,多保重,以后有空就回来看望您。”
谁知这一走竟是永别,在我离开故乡跟随妈妈到湖南衡阳的第二年,姥姥去世了,终年五十六岁。家里来信说,姥姥临终前一定要穿上妈妈给她的那件棉衣,并说自己走了,也不要告诉我妈妈,她工作忙,忠孝不能两全。姥姥一直拿着我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直到离开人世。想起和姥姥相处的点点滴滴,我痛哭失声,抹不掉的童年记忆,留下了一片深深的思念。那段时间我妈妈少言寡语,眼睛总是红肿的。
现如今,我都60多岁了,只有写一篇文章,在这清明时节怀念我的奶妈、我的姥姥还有我的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