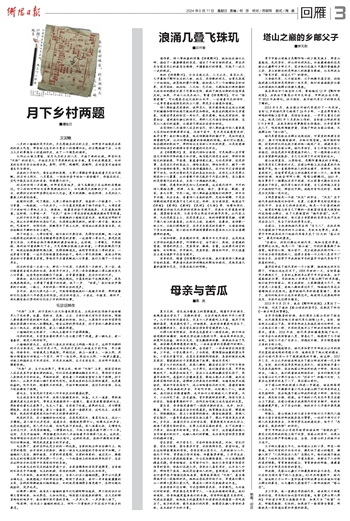■蔡 英
夏日炎热,苦瓜成为餐桌上的重要蔬菜。随着年岁的渐长,我越来喜欢苦瓜了,淡雅的清苦,正合历经风雨的中年人的胃口。儿子年幼时不喜苦瓜,长至十八岁便能吃上半盘,经历了残酷的高考,果然能吃苦了。仔细想来,我的母亲最爱吃苦瓜了,说是能解热清火,其实苦瓜暗合母亲贫苦操劳的人生。
记得儿时清明前后,母亲总在屋前点一棵苦瓜秧。秧子伸出胡须般的细藤时,她便在旁边插上数根竹竿,搭成简单的瓜架。初夏阳光旺盛,雨水亦充足,苦瓜藤精神抖擞,渐渐地长成了气候,满架都是郁郁葱葱的绿色。一朵朵金黄的花像精巧的喇叭,在南风里轻盈地吹响生命之歌。金花谢了,一条条细苦瓜悄然登场。少年说,小苦瓜像虫子;少女则说,像隔壁姑姑戴的碧玉耳坠。小苦瓜不置可否,在星光里渐渐肥硕起来,表面的皱纹也越发深沉,圆滚滚的肚子里像装满了故事。谁说不是呢?
家乡七夕的风俗是,夜深人静时,躲在苦瓜架下可听牛郎织女说话,听到的人有福气。七夕那天,我们翘首盼天黑,早早把晚饭吃了,把家务活做完了,然后三五成群地躲在苦瓜架下,张着耳朵聆听。湛蓝的天空镶满星星,像钻石般点点闪耀,南风送来荷花隐约的花香。老樟树上传来悠长的蝉歌,池塘里蛙声此起彼伏,深林中有夜鸟惊飞,远山回响着低沉的犬吠,屋檐有猫踩过碎瓦。那些幽微的声音,平时听不到,此时都入了心。渐渐地,我们相互依偎着睡熟,也不知什么时候被大人背回家。次日,小伙伴见了面,各自羞愧,皆不敢提昨夜的事。惟有竹架上的苦瓜,轻摇着翠绿的叶子,任阳光给它披上流光溢彩的衣裳。
霞光里,母亲轻笑着摘下一根根丰腴的苦瓜,洗净,切片,腌盐,挤水,然后盛在洁白的瓷盘里。她弯腰坐在灶前,劈柴烧火,待铁锅烧红,挖上小块雪样的猪油,煸香红椒蒜蓉,再倒入苦瓜轻炒,一盘青里透红的苦瓜就上桌了,像从中国画里走出来的。多年后,我看过齐白石的苦瓜图,寥寥数笔勾画的瓜架上,挂满了浓墨勾勒的苦瓜,瓜蒂上还有未落的黄花,瓜下还爬着一只草虫,极似童年的场景。苦瓜、豆角、茄子,这些蔬菜被填入当年孩童们的肚子,也融入他们的骨髓,成为其吃苦耐劳负重前行的精神力量。
苦瓜虽苦,却只苦自己,不会传染给其他菜。比如,苦瓜炒蛋、苦瓜火焙鱼,蛋与鱼并不苦,依然保持本色、浓香四溢。苦瓜这性情真像我的母亲。母亲在深山里长大,兄弟姐妹七八个,她处于中间,常常被父母所忽略,却最勤劳孝顺。小学毕业后,母亲主动为大家庭挑起重担,什么农活都抢着做,什么活都做得精益求精。母亲结婚后,生育孩子四个,她和父亲凭着不怕苦不怕累的蛮劲,将我们送进大学。母亲为人善良淳朴,从不与人吵架,哪怕受了委屈,她还是念着别人的好。直到现在,她还时常念叨着早些年谁借过钱给我家,谁帮我家搞过“双抢”,甚至谁帮她背过一段路程的米。她把这些品质传给子女,希望我们像大山一样博大宽厚仁爱大气,像溪水一样不忘来路奔流不息。
虽然母亲年过古稀,可还坚持种菜采茶,不肯歇气。无论我们何时回家,那菜园总是青翠可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我们回城时,母亲把蔬果塞满我们的车厢。母亲种的蔬菜自然好吃,吃进这些蔬菜,就把故乡的春夏秋冬和老家的风雨霜雪一同吃进去了。故乡的风雨,能长成我们的风骨,就像苦瓜融入母亲的身体,成为庇护子女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