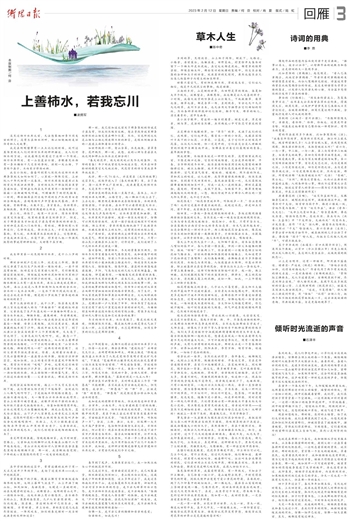■陈中奇
乡间的草,见缝就长。山上林子间隙,树底下,大路边,小路旁,房前屋后,池塘溪渠,田野菜地,村里除开大集体时留下一个晒禾坪是水泥地,其它处处都是泥地,都有草的绿野芳踪。即便在晒禾坪,那些陈旧的纵横的裂缝中,仍生长出散落的谷种和豆子的幼苗,就连屋顶的瓦缝间,居然也能长出几丛鸟儿衔落种子而萌生的细长野草。
好像只需空气,有时阳光都不用,草就能生长。它们让人相信,越是平凡到泥尘的事物,越是顽强。
江南的乡村,山是树的世界,而田野是草的领地。春夏和大半个秋天,放眼望去,满眼葱绿,永远都是让人欢喜的样子。小时候,我每天放学的任务是上山打柴火,下地拔猪草。柴草也罢,猪草也罢,都是杂草一堆。直到现在,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草,我叫不出名来,也无法用文字描摩出它们确切的形状,然而各种草的样貌却记忆犹新,触手可及。那草的味儿,清淡兼素朴,涩中生幽香。
在小孩子眼中,有这样一幅乡村图景:树是父亲,草是母亲,树与草,是活的自然课,共同构成心中可依恋可亲近的家园。
正是那些不起眼的草,如“草芥”的草,充满了我们的记忆。我观察,它们也开花,像苔米一样的小白花,或藏在深绿叶片底下的小红花、小黄花、小蓝花,至于它们什么时候花开花落,往往无人知晓,但一定是开的,它们在完全没人理睬欣赏的环境中自顾自地开放,仿佛在宣示着它们最艳丽的青春,最卑微的梦想。
照我理解,水稻原本就是一种野生的草。没有转黄成熟之前,不像是糊口之物,它长时间地绿着,完全是草的模样。早春,当犁铧刺进冬水田,把长在腐朽稻茬周边绒毛茵茵的嫩草翻耕过来,被沃土掩埋,成片开过紫红色花朵的草籽也成了沤肥原料。空气里湿气很重,暧昧的、暖暖的、照不透的阳光,草和泥土的味道,让人迷醉。我等待着移栽的秧苗,快快长满稻田,长到看不见田里的水,春风浩浩荡荡一吹,无比柔软地摆舞着嫩绿的细长叶片,形成一波又一波的绿浪,那时是最蓬勃,最美的。有时候,我低下身来,与秧苗平齐,眼界里便映满起起伏伏的绿意,心想,相比传说中北方那令人神往的一望无际大草原,也不过于此吧。
稻花很美!“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你注意到了吗?也许它是最朴素最实诚的花。我赶过禾花,许是四五月间,若干年前,我家搞杂交水稻制种。
稻田里,一条块一条块是稍低矮的母本,条块边缘间插着两排粗壮高挺的父本,自然长成一畦一畦类似菜地的规则形状。父本与母本花期大致相当。稻花细小,白色,只有牙签头大,含在裂胞而出尚空空如也的青色谷壳里。白天气温热起来时,谷壳会像蚌壳一样对半打开,两三根稻花蕊含羞似的,像花蚊子长长的细杆腿撑着一截棒槌身子,才怯怯探出头来。为提高受粉率,必须手动传粉,把父本的花粉赶出来,喂给母本。
每天上午大约九至十一点,太阳晒干露水,母本谷壳像鱼儿嘴似的张开口。各人手持一根长篙,伸到一排父本植株的腰际,猛地“嘭嘭”扑振两三下,你会看到一小股白色烟尘似的花粉飞腾出来,徐徐地弥散和飘落到母本植株上。天知道有多少花粉掉进了鱼嘴阵!我们高卷裤腿,赤脚踩在差不多齐膝深的烂泥里,水稻已与肩同高,人仅能露出头颈部,竹篙必须举着,防止碰落掉正在受孕的花粉。母亲往往头上扎一条白毛巾,手臂上戴着袖套,这样可防晒防虫防稻叶割手。赶一轮,爬上田塍,我们就躲到瓜架下的水渠里纳凉,弹掉头、肩上的花粉或小虫,清洗腿上篙上的泥糊,放松一阵。如此,一上午得赶上三四轮才能罢休。
稻花有股极淡的清香,几乎让人不易觉察,在太阳不太猛烈的早晨向中午过渡时最浓。当你身处水稻包围之中,闻到的更多是稻秆汁液丰沛的清甜味道,在那些张开口等着受粉灌浆的谷壳里,还有吐着的垂着的花信里,仿佛也嗅到一丝青涩的味道,一缕奶浆或米浆的味道。当太阳如火焰般炙烤时,你已被汗酸味、稻叶划伤皮肤的火辣感、热气冲进鼻腔的燥味所裹挟,已然闻不到稻花香了。
赶禾花的体验很奇怪,常让我既心怀敬畏,又窃窃发笑。我总是不由得类比,想起乡村猪、狗、牛、羊各色动物的配种,以及那些为配种焦急奔走的村民,当然也包括那些自学成才、无师自通、好像处于乡村下等人身份的专干配种这事的特殊乡民,他们大多是些脏兮兮油腻腻眯缝着眼睛的老大爷老太婆。每当排挞起轻烟一般的禾花,想着是在促成一场处在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的盛大无比、不可计数的受孕仪式,便有一股雄壮的声威,又有几分滑稽游戏的成分,那时我正是一个青春期的少年。世界如此神奇,阴阳共济,孕育万物,哺育万物,创造万物,一切始于花粉的微粒。
母亲认识一些草,当然比我识得多。每年春天,她都做艾糍,也到山上采草药,做酿酒的酵母。早春采艾草,实在是件普通随意的事,在家门口池塘堤岸上,在菜地田埂上,到处都是,随手能扯一背篓,掐尖尖,要多嫩有多嫩。艾叶表面青绿,叶背却灰白,毛绒绒的,草味重。母亲做的艾糍偏苦,放艾汁太多,蒸着不好吃,用糖煎到两面焦香,味道却一流。现在似乎苦的饮食越来越不受待见,母亲做艾糍就少了,也嫌麻烦,只有小妹回老家,一起兴兴头头做过一两次。母亲一直坚持自制酵母,因为每餐她都喝一两口酒,多为米酒。采来一种叫淡竹叶的草药,叶片似竹叶,但比竹叶宽大,色墨绿,叶面有层腊质,发光发亮,植株不是小灌木,而是草的样貌。同时还有另一种或几种草药,只记得里面必有一种满枝头开着米粒大白色小花的,有点像花店里常见的满天星,母亲说叫饼药——这显然不是确切的名称。我问,做酵母为啥总是这几味?从哪学的?她说上一辈传下来的,跟着做几次,不用学都会了。
事先磨出一大盆粳米与糯米按比例混合的粉子,再把这些杂七杂八的中药熬出来的黑不溜秋、药味刺鼻的汤汁浇进去,揉成汤圆般大小的白丸子,蒸熟再晒干,存在干燥阴凉处。要酿酒时,就取出几丸研成粉末,当酒曲撒在米饭上,和匀,盖上密封,过不了几天就能酿出甜酒来,屡试不爽,从无失手。我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停食,打馊嗝,每次只需泡发,烤几枚丸子吃,立马就应,真是神效。这种酵母丸子,煮来吃就成了土制汤圆,用糖煎来吃,又像糍粑,有一种适宜的中药香味。
在懂行的农民眼里,花花草草都是中药,什么部位可以吃,怎么个吃法,有什么药效,经过代代相传,他们都知道。最神奇的是,村里有人被蛇咬伤,被毒蜂叮咬,往往叫来会采解药的村民,它们在田间山头采几味中药,嚼烂敷在创处,患者不久即痊愈。解药究竟是哪几味草药,采药人却秘不示人。
各色各样的草里,我最爱野菊花。有一年秋天,不知出于什么触动,自己拎着一把小铲,漫山遍野去找寻,平时觉得很常见的野菊、到秋天便开出楚楚可爱小黄花的野菊,真要找时,跑了几个印象中的疑似地点,却一株也无。最后在山窝窝的坡上茶树旁发现一株,已粲然花开,挖回来移栽在屋后泥地里,没过几天竟然枯死了。真是,众里寻它千百度,得来殊不易,岂料它却不许我黄花数朵。假如有一天,我回村长居,一定在房前屋后种花,最好多种菊。
一花一草一世界,亦花亦草亦世界。人生一世,草木一秋,都是从田野中来,在平凡中生,一样植根土地,一样仰望星空。谁能否认花草没有生活,谁能否认花草没有梦想,谁能否认没有花草的世界必是荒漠般的苍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