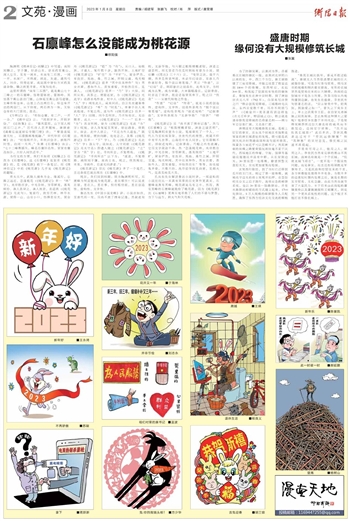■欧阳强
陶渊明《搜神后记·刘驎之》中写道:南阳刘驎之,字子骥,好游山水。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见有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囷,一闭一开。水深广,不得渡。欲还,失道,遇伐弓人,问径,仅得还家。或说囷中皆仙方灵药及诸杂物。驎之欲更寻索,不复知处矣。
这里所谓的“南有二石囷”,就是衡山七十二峰之一的石廪峰,俗称雷钵底、雷钵岭。其坐落于衡山县店门镇,山体延至衡山县马迹镇,主峰形似仓库,山崖上凸出两巨石,似仓库开启的两扇门,从下仰视,两石浑为一体,又似仓库的大门紧闭,故名。
《方舆记》云:“形如仓廪,有二户,一开一合。”《湘中记》云:“闭则岁丰,开则岁俭。”《总胜集》云:“暴风雷雨,山下居人闻闭石门之声。”历代诗人甚多题咏。唐韩愈 《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诗:“ 紫盖连延接天柱 , 石廪腾掷堆祝融。” 宋代毕田《石廪峰》诗:“时雨闻开合,年秋识俭丰。新陈四时雪,启闭一天风。”朱熹《石廪峰》诗云:“七十二峰都插天,峰名石廪旧名传。家家有廪高如许,大好人间快活年。”
为行文的方便,我们不如将《刘驎之》径改为《石廪峰》。这《石廪峰》是紧承《桃花源》的,是《桃花源》的下一条笔记。而《搜神后记》中的《桃花源》几乎是《桃花源记》的翻版: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桃花源记》多一“林”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渔人姓黄,名道真(《桃花源记》无此句)。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舟(《桃花源记》“船”为“舟”),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旷空(《桃花源记》“旷空”为“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桃花源记》前多“其中往来种作”句)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桃花源记》前多一“乃”字)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为(《桃花源记》无此字)设酒杀鸡作食。村中人(《桃花源记》无此“人”字)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难(《桃花源记》“难”为“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桃花源记》后多一“人”字)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桃花源记》“一一”后多一“为”)具言所闻,皆为(《桃花源记》无此“为”字)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桃花源记》后多一“下”字),乃(《桃花源记》无此“乃”字)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刘歆(《桃花源记》无太守名)即遣人随之(《桃花源记》“之”字为“其”字)往,寻向所志,不复得焉。(《桃花源记》“寻向所志”以下为:“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桃花源记》仅比《桃花源》多了一个尾巴,且这条尾巴就出现在《石廪峰》中。
现在,我们回到标题:同为陶渊明所写,石廪峰为何没能成为桃花源,差在哪里?可以说差在景,差在人,差在事,但归根结底,差在创造性、虚构性、文学性。
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讲: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胡应麟(《笔丛》三十六)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个说以寄笔端。”其云“作意”,云“幻设”者,则即意识之创造矣。此类文字,当时或为丛集,或为单篇,大率篇幅漫长,记叙委曲,时亦近于俳谐,故论者每訾其卑下,贬之曰“传奇”……实唐代特绝之作也。
“作意”“幻设”“传奇”,就是小说的创造性、虚构性、文学性。创造性表现为“假个说以寄笔端”,虚构性表现为“叙述宛转”“记叙委曲”,文学性表现为“文辞华艳”“俳谐”“特绝”。
《桃花源记》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与《石廪峰》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它是陶渊明有意为小说,笔端寄托了一个人、一代人乃至祖祖辈辈、世世代代的理想,荒诞不经中有平凡世界,山海经中有人间世;它虽篇幅不长,却叙述宛转,记叙委曲,尺幅之内有波澜;它虽文字简洁干净,然“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等等,却也摇曳多姿,大雅大俗,洗尽铅华而见诗意,见烟火气,见真美纯美大美。
孔庆东先生解读鲁迅小说时讲,一部虚构的小说往往比一本真有其事的历史著作更真实。石廪峰是真有其峰,桃花源是乌有之乡。然而,真有其峰的石廪峰就败给了桃花源,因为《桃花源》比《石廪峰》更真实地承载了人们的不堪与梦想,当下与远方,烟火气和天花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