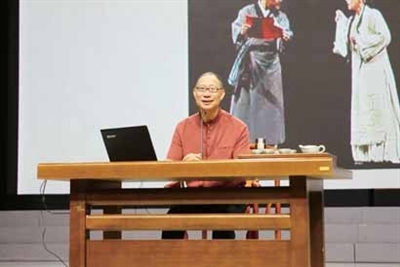在中国古代,打官司先要向官衙呈递诉状,由于当时的普通百姓中文盲较多,无法用文字来表述案情,于是,社会上就有人做起专门为他人代写诉状及其他文书的“讼师”。当时,充当“讼师”的既有赋闲在家的政府官员,也有不得志的读书人、举人等,还有在职的文武官员。他们可能为金钱利益而充当“挑词架讼”的讼棍角色,也可能因以法维权而赢得讼师的尊称,具有极强的两面性。
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度里,对于讼师这样的现象绝不能简而言之,它的出现和存在具有深刻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文化等意义。近日,本土文化学者邹鲁军做客船山故里·国学飘香——石鼓书院大讲坛·国学讲座,再谈古代讼师。
古代讼师社会地位比较尴尬
由于辩护在中国古代并不具备法律程序上的正当性,所以讼师在中国古代为政者或法律的视野中一般都不具备“良好”的形象,往往被视为添乱者与社会麻烦制造者。这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讼师存在价值的基本定位。
对讼师定位的表现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在传统的社会里面,讼师素来受人轻贱,他们的形象是贪婪、冷酷、狡黠、奸诈的,最善于拨弄是非,颠倒黑白,捏词辨饰,渔人之利。”例如,春秋战国时期郑国的政治家邓析,其被视为古代讼师的鼻祖。此人擅长诉讼,其辩论之术无人能敌,史书记载其往往“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并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而,邓析被当政者驷颛视为扰乱民心的祸首,惨遭杀害。
可见,古代“讼师”往往被视为影响社会和谐、挑词诉讼的不安定分子。从根本上看,这种对“讼师”品质低下的定位是由中国古代铁板一块的权力集权体制造就,并逐步灌输到了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法制文化。在这种文化传承里,根本就不承认讼师的辩护是一种崇高的工作,更谈不上对这种辩护工作悉心呵护,这导致讼师从事辩护工作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
“那个时候,讼师是封建专制权力结构的附属物,其不具有合法的资格,在诉讼活动过程中也没有合法的地位,不能公开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充当诉讼辩护人或代理人。他们不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专职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员,只能代人撰写诉状,解答有关法律问题,并没有发展到一种为社会广泛认可的公开职业。”邹鲁军说。
一方面,官府既痛恨又不得不倚仗讼师。儒家文化强调息讼,而讼师常常“挑词架讼”,价值观的对立使得讼师在官府眼中是“教唆词讼、拨弄是非”者,讼师也因此备受主流社会的垢病,常被讥为“讼棍”。虽然历代统治者在基本法典上规定了禁治讼师的法条,《唐律疏议》《宋刑统》《大明律例》和《大清律例》中皆有相应的条款,但又承认“书铺”的合法性,有时还不得不求助于讼师来解决纠纷,平息事态。所以,讼师总是禁而不绝。
另一方面,民众既离不开又讨厌讼师。由于被社会厌弃,导致不少讼师开始放弃自己的原则,变成唯利是图的小人,使得百姓更加厌弃他们。虽然百姓有时勉强尊称其为讼师、“大状”,但却常常用教唆词讼、颠倒是非、舞刀弄笔、架词越告、打点衙门、串通吏蠹、诱陷乡愚、欺压良善、恐吓诈财等贬斥之词来描写和形容他们的行为。而在被卷入讼事当中之后,不少百姓又不得不请求讼师帮助自身维权。
其实,讼师在古代法秩序中的作用,从一个方面来说,是应社会民众维护权益的需要而存在的,它不但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古代民主的进程,而且对古代的法制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从其另一方面看,因为这一职业不但不能够得到官方和社会主流价值的承认,反而被倍加指责和打击,更谈不上有什么行业管理或职业道德与纪律,这就难免使其陷入鱼肉百姓、架词越告、欺压良善的恶劣行为怪圈中。
讼师在古代法律中充当了重要角色
诉讼文化是法律文化的下位概念,讼师文化又属于诉讼文化的范畴。
因此,讼师文化可以定义为:在以专制集权为核心的中华封建法律体系下,讼师群体在运用法律知识改造社会的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总和。包括讼师行为文化、讼师物质文化、讼师制度文化和讼师精神文化。
那么,讼师文化的内涵又有哪些呢?
其一,讼师的精神文化。该种文化是讼师群体在法律实践过程中受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影响而长期形成的一种文化观念和精神成果。讼师以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和价值观解决法律实践问题,是讼师文化的核心。其主要通过讼师价值理念表现出来,包括讼师价值观、讼师精神、讼师理想、讼师道德、讼师哲学等几个方面。
其二,讼师的行为文化。这种文化是讼师群体在一定行为规范的制约下,在法律实践中产生的、以人的行为为形态的实践文化。讼师怎样从事法律实践问题,是讼师文化的外显,主要通过讼师行为规范表现出来。如,为确保诉讼得胜,讼师要对讼事进行谋划。谋划的主要环节是精心拟写诉状,以求通过状词达到获胜目的。因而有的讼师,竟调唆求助者制造某种假象或事端,以改变情节或渲染案情而加强状词的说服力,使其诉讼获胜或逃脱惩罚,等等。
其三,调解也是讼师文化的重要内容。调解息讼可以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因此历代官方从中央到地方都大力提倡调解。然而,调解也易产生弊端,即在客观上为乡保和衙役滥用权力提供了机会。当事人为了避免乡保和衙役的鱼肉,也为了争得合理的调解结果,于是便委托一些声望较好的讼师为中间调解人。
其四,讼师还可以教习诉讼,这在宋朝成为常见的现象。应该说,法律知识得以普及,也有讼师的功绩。
“讼师秘本”是被歪曲了的法学教材
和“讼师”在同一个时期产生的还有“诉讼秘本”,《两便刀》和《萧曹遗笔》等就是清代“讼师秘本”。
何为“讼师秘本”呢?就是讼师们在经过深入研究之后,采取深入浅出的方式,把诸如敕语御批和所告各类律话套语摘录出来,编成歌诀,便于诉讼当事人掌握运用。此类讼师秘本编排生动,应用效果明显。同时,它以案说法,精选法律条文和法律术语,配以相关案例的诉词、辩词和判词,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体例,是公案小说的雏形。
“讼师秘本”主要体例如下:收集曾经发生的案件,添入相关控诉、抗告的状词,做成应用范本。同时,将不同刑案分门别类,一般分为人命、奸情、贼盗、婚姻田产、户役、骗害、斗殴、立继等类。这些编印内容当然是为了用于打官司,被假想为打官司“被告”身份的对象,主要是一般平民,但也包括以贪官、污吏、豪强为对象的被告。另外,不少讼师秘本也收集助人申请官方执照文书的写作范本。这些内容含有大量的法律知识,因而为民间所重视。然而,与民间重视这类法律知识的态度相反,不少明清官员都十分敌视这些讼师秘本。
从本质上讲,“讼师秘本”也是一种法律读本,是封建专制体制下被歪曲了的法学教材。尽管官方不承认它的合法性,但它却是严格按照官方标准法律文本来解释法律知识和研究诉讼技巧的。它一方面有广泛的社会需求市场,另一方面又处于非法地位。官方一厢情愿禁毁讼师秘本,而它却一直在民间广泛流传,甚至对于今天的法制文明推进,也具有十分可贵的借鉴价值。
说到底,古代讼师的进步性应略大于其落后性。讼师职业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行政等一系列制度的必然伴随物,是封建专制社会民主性因素不断进步的表现特征之一。这一职业的发展绝不是偶然式和零敲碎打式,作为正式制度尤其是封建法律制度的补充物,讼师其实始终在一种非正式制度形态存在并不断壮大。它的主要社会功能是使统治阶级的法观念和被统治阶级的法观念统一起来,它的主要舞台是民众和法律的边缘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