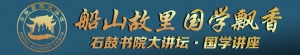秦律初步确立了古代法律体系
■文﹨本报记者 许珂 图﹨本报记者 罗盟
中华法系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战国时期是由早期习惯法向成文法转变的重要阶段,而秦汉则是中国古代成文法法律体系的全面确立时期。
子产铸刑鼎,第一次将法律面向民众公开
公元前543年,在大夫子皮的保荐下,41岁的子产开始担任郑国的“当国”之职(类似于宰相),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执政生涯。在这期间,他发挥了高度的政治才能。
子产改革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是公元前536年的“铸刑鼎”——把惩治罪犯的刑律铸在金属鼎上,向全国老百姓公布。这是中国政治史、法制史的一件大事。
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举措。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说,春秋时期,上层贵族社会认为刑律越隐蔽越好,决不能让国人知道。这样才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老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这当然是一种古老专制时代的遗迹。
子产决心打破这种愚昧,他对已有的刑法加以修改,在这个基础上主持编订了三种刑法,并将其公之于世,让老百姓明白法与非法的界限,知道犯了法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这无疑是进步的法制理念,当然也打击了贵族特权。子产这个做法,遭到很多贵族的反对。
晋国大臣叔向专门为此给子产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信中说,本来民众怀着恐惧之心,不敢随便乱来。你把法律公布了,民众就会钻法律的空子,争相琢磨怎么做坏事而不至于被制裁,这样就不怕长官了,反而会导致犯法的事情越来越多,腐败贿赂到处泛滥,郑国也会因此而完蛋。
子产顶着晋国压力,给叔向回了一封信说:“我为的是救世啊!”他表示要坚定不移地公布法律。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不错,社会治理透明度增加,大众欢迎,犯罪案件减少。再说,郑国注重商业,过去贵族利用刑罚的随意裁量权,压榨商人和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对国家很不利。子产公布法律,限制了贵族特权,促进了郑国农业和商业的发展。“铸刑鼎”这一重大改革措施符合社会发展的新需求。
子产以后,郑国又有邓析,造新刑法写在竹简上,号称竹刑,为郑国所施行。战国时韩国则出现了著名的法家人物申不害(韩灭郑后,郑韩合一),推行术法治国。因为郑国社会在东周时期变化最大,法家学派正是代表商人和新兴地主利益的学派,郑国成为法家学派的中心产地,不是偶然的,归根溯源,子产正是法家学派的先驱者。
韩非主张“立法于君”,除国君外一律要受法约束
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出生于战国末期的乱世中,他的学说融会贯通并发展了老子、荀况以及商鞅等人的思想,形成自身的法家理论。他的著作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现存《韩非子》五十五篇,大体上可以说是韩非学派的著作汇编,大多数是韩非子的著作,反映了韩非的思想。
韩非主张“立法于君”,强调立法权的集中。他认为法是由国家来编订,让官府来具体设施,并让老百姓周知和遵守的规范。这样一来,举国上下,事无巨细,一切决断于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韩非的思想并不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在他那里,“人人”是不包括君主的。他曾说过“君不同于群臣”、 “君臣不同道”,在君主面前,人人都要绝对服从君主。因此,韩非的“法”实则是把法律绝对化,也就是把君主绝对化,树立君主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
韩非一生追求的政治抱负是为统治者创建一套完善而行之有效的“王者之道”,这就是其以“法”、“术”、“势”为核心的法治理论。概括地说,就是君主立法、驭术、凭势来统治臣民。这套学说,适应了战国新兴地主阶级建立大一统帝国的统治需要,也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政治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
其中,“术”就是权术,是君主驾驭、使用、考察臣下的手段,其主旨便是以权术施谋诈,亦即阴谋诡计。术与法的显著区别在于,法是向国人公布的,术是藏在君主的“胸中”的,是维护君主专制的驭臣之术。虽然这种非常规手段对于防止分裂、维护中央集权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其总体上是阴暗的,它的消极影响还是占主导地位的。“势”主要指君王手中的权势、权威或君主统治所依托的权力和威势。
韩非认为,法治的对象是广大的臣民。所谓“法不阿贵”,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意思就是说,除了国君以外,不论贵贱,一律要受法的约束。一方面,他主张论功行赏,反对无功受禄,不论贵族小民,只要立下功劳,就可依法受赏,加官加爵。另一方面,他认为法治的精神更重要的在于罚,而且是重罚。
总之,韩非“以法为本”的法、术、势三者结合的法治思想,是在战国末期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在封建社会早期法治建设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应当说是一种思想上的进步。消极成分在于其鼓吹专制、反对德治、权谋诈术等。但总体来看,他的法治思想为秦的统一提供了理论基础,对以后两千多年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商鞅两次变法,为秦一统天下打下坚实基础
战国时期,各国为了确立封建统治,发展封建经济,先后在各国掀起“变法”运动。当时,商鞅通过推行“连坐法”、“分户令”、“军爵律”,改革土地制度、重农抑商、奖励军功、推进县制,使得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的数年间,国富民强,天下无敌,最终消灭六国、统一中国。
“徙木立信”是商鞅变法的坐标。“商鞅以微小的代价树立了秦国法律的权威,改变了秦国政府在百姓心中的政令反复、固有守旧等印象,为后续变法确立了有法必依的基调,保证了后期各项法令的顺利颁布与彻底贯彻执行。自此之后,守法有功者赏,违法有罪者刑,这就是强秦变法。”邹鲁军表示,徙木立信提升了秦国政府的公信力,树立了秦国新法的权威,确立了有法必依的法律精神,让秦国老百姓看到了政府的新气象与革新的魄力,同时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也保证了百姓对法令的信服程度、敬畏程度与执行效能。
期间, 商鞅大规模地推行过两次变法:
第一次变法在公元前356年。这次变法的主要内容有:颁布法津,制定连坐法,轻罪用重;奖励军功,建立二十等军功爵制;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强调“以法治国”,要求国家官吏学法、明法,百姓学习法律者“以吏为师”;改法为律,强调法律的普遍性,具有“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的功能;轻罪重罚,不赦不宥,主张凡是有罪者皆应受罚;鼓励告奸;用法律手段剥夺旧贵族特权;强化中央对地方的全面控制,剥夺旧贵族对地方政权的垄断权。
第二次变法在公元前350年。这次变法的主要内容有:废井田,开阡陌,谁开垦荒地,就归谁所有。土地可以买卖;建立县的组织,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组织成县,由国家派官吏直接管理;为了便于向东发展,把国都从原来的栎阳迁移到渭河北面的咸阳。
这样大规模的改革,当然要引起激烈的斗争。许多贵族、大臣都反对新法。有一次,秦国的太子犯了法。商鞅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必须上下一律遵守。要是上头的人不能遵守,下面的人就不信任朝廷了。太子犯法,他的师傅应当受罚。”
结果,商鞅把太子的两个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都办了罪,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上字。这一来,一些贵族、大臣都不敢触犯新法了。
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迅速超越关东六国,为日后横扫六国、一统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商鞅为历史的前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斯创制秦律,初步确立中国古代成文法法律体系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李斯等人的辅佐下,统一了六国,结束了纷乱的战国,建立了大一统的大秦帝国,然而,历经战乱后的九州百废待兴,陡然辽阔起来的疆土并不是那么容易治理的。六国的封号虽已不在,他们统治过的痕迹却依然明显。各地区通行着不同的法令,这对大秦帝国的统治管辖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于是,修明法制,制定律令,令天下遵守统一的法律,成为摆在秦始皇和李斯面前的一件当务之急的大事。
作为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奠基者——李斯,在秦统一之后,参与制定了秦朝的法律和完善了秦朝的制度,力排众议主张实行郡县制、废除分封制,提出并且主持了文字、车轨、货币、度量衡的统一。在指导思想上,秦王朝奉行的是法家的“法治”、“重刑”等理论,皆与李斯分不开。
秦王政元年时,韩国派了一个叫郑国的水利专家到秦国来修长达三百余里的灌溉渠,企图以此来消耗秦国国力,不东伐韩,被秦发觉,要杀掉他。郑国说:“臣为朝廷数年之命,就渠成亦秦万世之利也。”终于让他完成这件工程,然而那些因为客卿入秦而影响自己权势的秦国贵族就利用这件事情对秦王进行挑拨,说外来客卿入秦都是别有用心的,应该把他们都赶跑。秦王政十年,秦王下令驱逐所有客卿,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于是他就写了这篇《谏逐客书》,劝谏秦王不要驱逐客卿。
文章从秦王统一天下的高度立论,反复阐明了驱逐客卿的错误,写得理足词胜,雄辩滔滔,因此打动了秦王,使他收回了逐客的成命,恢复了李斯的官职,而《谏主客书》也就成为一篇脍炙人口的名文,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所传诵。
逐客一事就像是一次试炼,而结果君臣双方都很满意,秦王从此视李斯为臂膀,李斯也没有辜负始皇的期望。
期间,秦国推行郡县制的命令已下达有七八年之久,此时却仍有人反对,李斯十分气愤,即上书秦始皇。建议秦始皇下令没收《诗经》、《尚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使天下人无法用古代之事来批评当前朝廷。这就是著名的“焚书”事件。
“焚书”之后,始皇和李斯意识到了没有统一的法令,是根本办不成大事的。于是,在李斯的建议下,秦始皇废除了以往六国的律令,制定了通行全国的统一的法律,就此中国古代成文法法律体系初步确立。
邹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