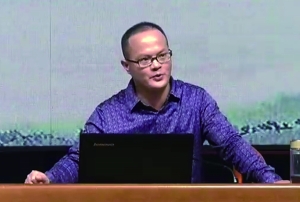参观过湘西草堂的市民都知道,王船山的故居里有一幅自题壁联,就是众所周知的“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这是王船山对自己一生经历与努力的自我总结,志在总结批判传统儒家哲学,并在此基础上开辟新的思路。近日,“注目礼学说”创始人、世界创客大会发起人欧阳君山做客国学讲座,为大家讲述王船山的大智慧和豪杰人格。
欧阳君山认为,对联的前一句是说自己致力于儒家的学术研究,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进行了详尽的研读、评注和创新;后一句的意思是明朝亡了,七尺男儿岂能屈服。“从天”是指明朝的灭亡使自己心灰意冷,“乞活埋”就是说不怕清政府的压迫。整体两句就是表现自己的民族气节和人生追求。
“六经责我开生面”体现了王船山非凡的学术使命与成就
要说王船山的学问,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渊博,400余卷、800余万字,可谓皇皇巨著。从《船山全书》的内容看,包罗万象,于天人古今无所不涉,以至有论者称“王夫之或许是中国文化史上集大哲学家与大文论家于一身的孤例”。
欧阳君山表示,“六经责我开生面”这一句则正好体现了王船山非凡的学术使命与成就,而其学问最鲜明的四大特征就是“一、正、实、达”。
王船山的学问具有“一”的特征,这里可称为一元论。这首先表现在王船山把世界归结为“气”,气是世界的一元本体,万物皆由气而“化”。同时,王船山的一元论更表现在弥合种种二元对立,从二到一,化二归一。如,天理与人欲,王船山就明确表示“理寓于欲中”,“天理与人欲同行”,“终不离人而别为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又比如,权术与仁心,王船山也反复申明“术不在仁之外”,“有其心而术固具其中也”。
王船山学问给人的第二个印象应该是“正”。所谓“正”是“大本大源”,就是正派、正宗、正气、正大。“群经之首”的《易》被王船山当成了大本大源,不仅有“《易》者,天地固然之撰也”的明确说法,而且有“道盛而不可复加者,其惟《周易》乎”的深沉感慨,事实上也构成王船山心目中的正学之源。
“实”是王船山学问的深邃内涵,意思就是要有旗帜鲜明的唯物主义甚至实证主义。具体讲,有两个关键点彰显了王船山学问之高度务实,一者“依人建极”,一者实践理性。“依人建极”,就是理论不能够脱离人,而必须立足人、依靠人、为了人、服务人、验于人,理论一旦脱离人,无论高大上,还是低劣俗,必流于虚妄,因为与人无关了;“实践理性”是西方哲学的概念,意思是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纵观王船山的学问,真正高明之处应该主要表现于达。所谓达,就是通达,尤其指人情练达。在史论中,至少有三个方面能彰显王船山的知人晓事之达。首先,王船山强调坦然平情,其以人论史,不仅把人的因素摆在第一位,更把人的政治成熟度尤其是“平情”作为人的因素的核心,这充分表现在王船山对所谓“大臣之道”的论述中,他通过论史对历史上的有名大臣作了个分类,包括清高之士、直谏之士、意气之士、功名之士、刻核之士、矫诡之士、鄙陋之士,其实都是情商有欠缺的人;其次,王船山强调“大中至正”。他认为,不仅做人要大中至正,而且也是机权的根本;其三是审时度势,就是为人处世不仅讲实力、讲道理、讲正气,而且讲时机,即便理直气壮,甚至胜券在握,也不轻举妄动,而是待时而动,见机而作。
“七尺从天乞活埋”唱响了王船山的豪杰人格
王船山有部著作叫《俟解》,里面有一句名言——“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这句话的意思是,豪杰的人未必做得上圣贤,圣贤的人一定做得成豪杰。
首先,王船山有着拯救时代的恢宏志向。在修养上,他十分强调立志的作用,认为立志是人生的大本大源,所谓“志是大纲趣向底主宰”。他认为“志”是决定性的主宰,所谓“人品之大小之不齐无他,唯其志量而已”。王船山不仅有“故国余魂长缥缈,残灯绝笔尚峥嵘”的不屈,而且有“千年欲识丈夫心,独上危峰揽苍翠”的高昂。
其次,王船山有着向死而生的壮烈情怀。王船山生于明万历年间,但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倾覆,崇祯皇帝煤山自缢,王船山闻讯后数日不食,作《悲愤诗》一百韵。在“反清复明”屡败而无望后,从此以明王朝遗民自居,并转而从文化入手,希望以著述讲学图文化复国,实现“用夏变夷”,对吾国吾民吾文化,情怀壮烈。实际上,在弃戎从文、隐居大罗山一带后,王船山已然向死而生,是“我自从天乞活埋”的“活死人”。
正因为王船山对吾国吾民吾文化向死而生的壮烈情怀,感天动地,成为中华历史和中华文明的精神火种。谭嗣同的老师刘人熙就明确赞先生的风骨为“兴起中国之种子”。
第三,王船山有着直取百世的献祭精神。这种精神主要表现在王船山的理论自信,豪迈跨越时空,追求“吾书两百年后始显”。即是说,王船山在近四十年的隐居著述,不是为当时当世的注目礼,而是直取两百年后的“来世报”。
由此可见,王船山称得上圣贤学问与豪杰人格的高度统一。而湖南人在近现代中华历史中所表现出的血性,有着王船山 “七尺从天乞活埋”的强大加持。如,面对挥向维新者的屠刀,原本也可以东游他乡的谭嗣同毅然舍生取义,令人无法不联想到王船山的豪杰人格,他在狱中所题“我自横刀向天笑”形式上也极像王船山“我自从天乞活埋”。
船山学说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底色
天崩地裂的朝代剧变,铸就了王船山高尚而坚强的爱国人格,也激荡出其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他一生以“六经责我开生面”自期自许,为传统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许多历史性的总结和创造性的贡献,努力开创了古代哲学的新纪元。清初学者刘献廷评价他:“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之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
王船山的著作在清朝前期200年是“若存若没,湮塞不行”。到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由王船山六世孙王承佺交付邓显鹤校阅、邹汉勋编辑、刊刻《船山遗书》,并编撰了《船山遗书目录》,第一次把王船山提到与顾炎武、黄宗羲、李颙等明清之际哲学家相颉颃的地位,而船山之学开始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
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一支军队会和一门学问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曾国藩统率的湘军例外。不但他本人手不释卷地研读船山学说,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以求治国用兵之道。湘军的高层将领中也弥漫着浓郁的王学氛围,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在金陵设局刻竣《船山遗书》,共收著作56种、322卷,船山学说受到全国尤其是湖南士人的高度尊崇,对近代湖南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底色。
湘籍著名经世派学者、中国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倡建岳麓书院船山祠。光绪四年(1878),衡阳县令张宪和为崇祀乡贤王船山,在王衙坪王氏宗祠始建船山书院,是中国最早以“船山”命名的书院。光绪十七年(1891),衡州知府窦世德根据彭玉麟生前遗愿,礼聘湘学泰斗、天下第一才子王闿运出任船山书院山长,很快使之成为晚清中国十大书院。梁启超指出:“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夫之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辛亥革命以后,刘人熙等在长沙曾国藩祠创办船山学社,发行《船山学报》,产生了很大影响。1921年,毛泽东、何叔衡在此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称赞王船山“开一代风气之先”,“对湖南学风有着巨大的影响”。
如今,船山学说已经成了一门显学,不仅在中国,日本、新加坡、韩国都有研究船山学说的机构和专家学者,美国、俄罗斯和欧洲各国都有船山论著、诗文译本,王船山的学术遗产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1985年,美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评出古今八大哲学家,其中四位唯物主义哲学家依次是:德谟克利特、王船山、费尔巴哈、马克思。美国著名学者裴士锋的《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一书称王船山是湖南人的精神领袖。著名哲学家张岱年称王船山是“中国古典哲学唯物主义的最高峰”。
欧阳君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