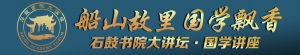纵观古今中外发展的历史,治理国家从来都离不开严峻的法治和良好的德治,很少出现过纯粹的“法治”状态或“德治”景象,只不过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现实需要或轻或重,或偏或倚。
“德治”与“法治”究竟孰轻孰重?近日,市委党校法律教研室教师李霞做客国学讲座时告诉大家,如今,要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离不开“德法兼治”的治国方略。
古代的“德法”经历了从君权神授到以德配天的转变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尚书·尧典》
“自尧帝起,我国就已开启了原始德与法的萌芽。”现场,李霞向大家解释,以上这句话的意思是:考查古代传说,帝尧的名字叫放勋。他严肃恭谨,明察是非,善于治理天下,宽宏温和,诚实尽职,能够让贤,光辉普照四面八方,以至于天上地下。他能够明察有才有德之人,使同族人亲密团结。族人亲密和睦了,又明察和表彰有善行的百官,协调诸侯各国的关系,民众也随着变的友善和睦起来了。
以此看来,在我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德治思想,并形成德治传统。
关于德治的记载,最早成书于周代的《诗经》《尚书》中。《诗经》不少诗篇蕴含着前代圣贤以德治国的思想,《尚书》中提出了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的命题。要保住天命,就必须敬德,以祈天永命,勤政爱民,得到民众的真心归附。
而德治思想的另一含义是“明德慎罚”。
在商代达到顶峰的神权法思想,被西周统治者继承发展,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周公旦等为代表的西周奴隶主贵族,总结并吸取了夏代、商代灭亡的教训,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君权神授说。
他们认为,“天”或“上帝”不是哪一族独有的神,而是天下各族共有的神;“天命”属于谁,就看谁有能使人民归顺的“德”。“上天”只会把统治人间的“天命”交给那些有“德”者;一旦统治者失“德”,也就会失去上天的庇佑,新的有德者即可以应运而生,取而代之。因此,作为君临天下的统治者应该“以德配天”。
李霞告诉大家,在“以德配天”的基本政治观之下,周初统治者具体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法律主张。“明德”的要求,主要包括三个基本方面:敬天、敬宗、保民,也就是要求统治者恭行天命,尊崇天帝与祖宗的教诲,爱护天下的百姓,做有德有道之君。“慎罚”的要求是用刑谨慎、宽缓。
也就是要求,统治者首先要用“德教”的办法来治理国家,通过道德教化的办法使天下人民臣服,在适用法律、实施刑罚时应该宽缓、谨慎,而不应一味用严刑峻法来迫使臣民服从。
德治以儒家“德主刑辅”为理论, 法治以“以法治国”为根本
在经历了社会稳定——生产力发展——土地私有——宗法制度破坏等之后,我国进入了乱世争雄时代,而德治、法治理论也开始系统化。
汉代中期以后,“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主张被儒家发挥成“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基本策略,从而为“礼法结合”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法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李霞说,孔子继承周代的德治思想,强调治国要以礼乐为核心,突出教化作用。社会秩序井然,人们和谐相处,是孔子希望通过德治达到的理想状态。战国时,沿着孔子的思路,孟子又提出了一系列仁政主张。他主张以德服人,反对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提倡省刑罚,教育百姓做到孝悌忠信。
西汉初,陆贾告诫刘邦,提出了治以道德为上的观点。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代德治思想定下了基调。他认为,治理国家不能只靠刑罚,要通过教化培养人的是非荣耻之心,德治思想成为政治领域的主导思想。
唐朝前期,隋朝二世而亡对唐初君臣是严厉的警示。唐太宗说: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既要发挥道德教化的作用,也要发挥法律的制约作用,二者不可割裂,互为补充。在刑罚的施用上,唐初务在宽简。在唐太宗等人德治思想影响下,唐高宗、武则天时期,遵循先人遗训,缓刑用仁,谨慎治国,天下大治。
“而当时的‘法治’思想,则体现在法家以法治国的基本原则上。”李霞告诉大家,法家是先秦诸子中的主要派系之一,他们对法律最为重视,其对人类社会影响最为深重的主张就是“以法治国”,突出法律这种国家的强制性工具在社会统治中的绝对准绳。
如,在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齐国的法治思想独树一帜,被称为齐法家。齐国是“功冠群公”的西周王朝开国功臣姜太公的封国,姜太公的祖先伯夷辅佐虞舜,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创始礼法并用的制度。太公封齐,简礼从俗,法立令行,礼法并用成为齐国传承不废的治国之道。管仲辅佐齐桓公治齐,一方面将礼义廉耻作为维系国家的擎天之柱,张扬礼义廉耻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以法治国,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的人。
又如,先秦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他主张:“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意思是“智者制定法律,蠢笨的人被此制约无法创新;贤能的人根据时代变更礼仪,庸才拘泥于此” 。
与此同时,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韩非子更是提出了“以法为本,法势术并用的法治布局”。 所谓“法”,即吸收李悝、吴起、商鞅关于“法”的思想,将其“编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的成文法典; “势”,即君主要握有权力,有了权势才能统治人民;“术”,是指君王统治的手段和策略。
以德治国是依法治国的基础,依法治国是以德治国的保障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这是《过秦论》中贾谊对秦朝灭亡原因的总结。李霞认为,这也是单任法治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没有实行仁义,而使攻守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德法结合,其价值内涵的融合应为“大德小刑”,其制度层面的融合应为“德本刑用”。
如,《刑案汇览》记载,龚奴才因妻与人通奸,争吵斗殴,以剪刀刺陈氏,陈氏闪避,适龚父加红赶来劝解,收手不及,误将龚加红左肋刺伤。浙江巡抚就此案是否适用存留养亲曾上报请示刑部,案件判决几经曲折,朝野内外有很大影响。最终,道光元年十月初一,道光帝下达圣旨,称考虑龚奴才之父母均年逾七十,家无次子,值得同情,且龚奴才素来孝顺,又系误伤,故准其存留养亲,同时申明此系法外施仁,下不为例。误伤父亲的龚奴才最终得以存留养亲。只有一子的龚加红夫妇老有所养,这都归功于“存留养亲”制度。
不可否认,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法治社会,但法律并非万能,再详细缜密也必有疏漏之处,法治在一定意义上存在着盲区。而道德是人类自我完善的精神自律,引导人们在广泛的社会领域自觉地遵循社会行为规范,往往能够起到“法治”所不能有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若仅有法治而无德治,人类社会“绝对不是一幅完美的图像,甚至还可能表现出某种异化的、冰冷的面貌”。
对此,李霞表示,真正的“德法”关系应该是不可偏一而用、不可简单结合。简而言之,道德是人类文明自发形成的意识框架,法律是国家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行为规范总和。
综上所述,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来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劝导力及社会舆论的引导来规范、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法治是他律,道德约束是自律。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只有将法治和德治结合并用,实行德法兼治,有力地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才能使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朝着健康、正常的轨迹发展,才能把我们的社会真正引入和谐社会。
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