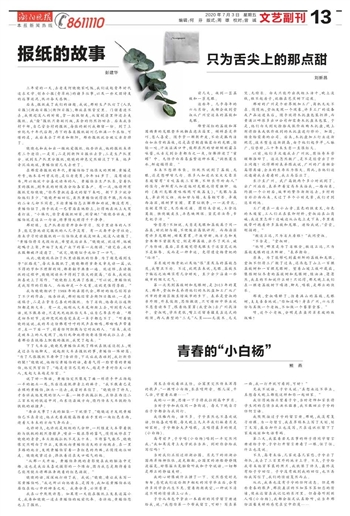前几天,收到一筐荔枝和一筐龙眼。
这些年,几乎每年的六七月份,我都会收到堂叔从广州空运来的荔枝和龙眼。
绛紫深红的荔枝和浑圆褐黄的龙眼整齐地躺在泡沫箱里,模样甚是乖巧,惹人喜爱。随手拿一颗剥开皮,不论是瓤肉洁白如冰雪的荔枝,还是晶莹剔透偏浆白的龙眼,轻轻一咬,汁液溢满口中,馥郁浓烈的甘甜倾刻霸占味蕾,从舌尖到全身都为之一爽,仿佛掉进了“蜜罐”中。无怪乎白居易盛赞这种水果,“润胜莲生水,鲜逾橘得霜。”
本来不想掉书袋,但既然说到了荔枝、龙眼,还是想啰嗦几句。很多人知道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留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佳句,却鲜有人知道他对龙眼也情有独钟。他的《廉州龙眼质味殊绝可敌荔支》,“龙眼与荔支,异出同父祖。端如甘与橘,未易相可否。异哉西海滨,琪树罗玄圃。累累似桃李,一一流膏乳。坐疑星陨空,又恐珠还浦。图经未尝说,玉食远莫数。独使皴皮生,弄色映琱俎。蛮荒非汝辱,幸免妃子污。”
啥意思?不细说。大意是龙眼和荔枝属于同一品类,好比柑与橘,不便做出高低评判。而西海滨有许多龙眼树,硕果累累,汁液甘甜,地方志和美食书都不曾提及它,倒是那荔枝,出尽了风头,被广为传颂。最后,苏东坡觉得龙眼生于这蛮荒之地不是耻辱,反而是一种幸运,免得遭受杨贵妃的“玷污”。
苏东坡对杨贵妃以及他“恨”屋及乌的荔枝态度,我暂且不论。不过,就现在来说,龙眼、荔枝生于偏远之地确实有几分好处,至少会少沾染一些城市的烟火之气。
第一次见到荔枝树和龙眼树,是2013年的夏天。那年,堂叔和表弟将他们的木托盘加工厂从广州市的黄埔区搬至增城市的乡下。表弟是堂叔的亲外甥,外表俊朗,思维敏捷,只可惜初中毕业就不愿意读书了,跟着他舅舅(我堂叔)去广州找活干。堂叔呢,学历更低,嘴上还留着撮吴孟达式的胡须,两人典型的“三无”人员——无技术、无文凭、无特长。白天只能外出找短工活干,晚上没钱,租不起房子,就躲在芭蕉树下过夜。
那时的广州是个世界级加工厂,商机无处不在。慢慢地,堂叔发现一个现象,许多工厂的设备或产品运进来后,随手就将木托盘包装扔掉,而黄浦江畔很多出口公司却需要木托盘来包装。于是,他们白天到处捡拾或低价收购木托盘,晚上则将捡来或低价收到的木托盘进行修补、加固,转卖给需要的公司。后来,木托盘加工行业逐渐规范,技术壁垒逐渐提高,由于他们起步早,人脉广,信誉好,二十年来生意一直很红火。
以前,他们多次邀我去广州玩,因怕舟车劳顿都推辞了。这次忽然搬厂,是不是经营出了什么问题?记得那时表弟跟我说,广州的厂房租金高得离谱,企业的生存压力很大。因此,当他们这次邀请我去看看时,我立马答应了。
长沙至广州,武广高铁两个多小时就到了。出广州站后,表弟开着宝马车来接我,一路向东,约摸一个小时后,城市的繁华渐渐远去,乡村的古朴扑面而来,又过了半个小时光景,我们才到达目的地。
工厂建在一座小山旁,蓝色的铁皮瓦,白色的木棱窗,工人们正在装卸材料,堂叔站在山岗喊:我这里怎样?边喊边从山包上走下来,手里连枝带叶抱着许多荔枝和龙眼,递给我说:“尝尝,刚摘的。”
“搬这么远,只为省点房租?”我问堂叔。
“不全是。”堂叔回。
“他呀,哪里是为了省租金,搬这么远,只为荔枝龙眼的这点鲜甜。”表弟抢白。
原来,为了能够吃到最新鲜的荔枝和龙眼,堂叔不但将工厂搬了过来,还承包了山上一百棵荔枝树和一百棵龙眼树。望着山坡上枝叶葳蕤,像桂树似冬青的荔枝树和龙眼树,绿油油、蓬蓬然,我真的不知说什么好!只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在一棵老荔枝树下喝酒、聊天、唱歌,是那么的快乐。
那夜,堂叔喝醉了,指着满山的荔枝、龙眼树,支支吾吾地说:“你知道吗?身在广州,六七月份与其做一个老板,不如做一个饕餮食客。”
呀,这个小老板,分明是在盗用苏东坡的版权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