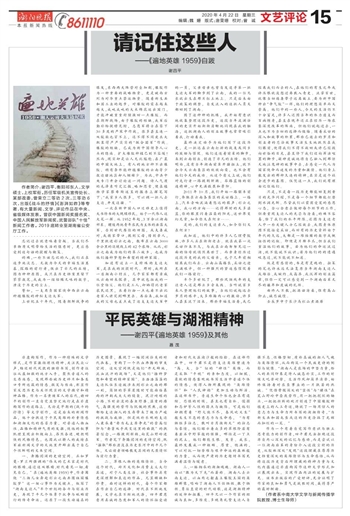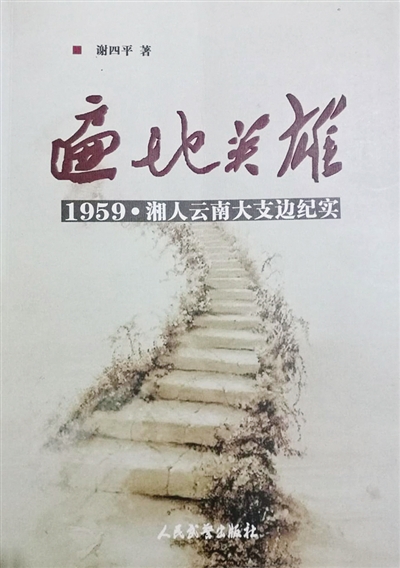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当我们尽享物质文明带给生活的惬意时,更应感受到这句话的提醒与鞭策。
的确,一些不该忘记的人,我们正在逐步地淡忘。无数为今天的幸福生活奠基、探路的前行者,做出了非凡的业绩,因为种种原因,或只在历史档案里留下寥寥数笔,或成为一组枯燥无味的数字,湮没于历史的尘土。
譬如,一支肩负国家使命西出云南种植橡胶的神秘支边大军。
上世纪五十年代,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东西两大阵营对垒加剧,橡胶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更是被西方列为对华重点禁运物资。随着新生共和国工业的起步,对橡胶的需求越来越大,成吨成吨的大米棉花运出国门,才能冲破重重封锁换回一点橡胶。而在朝鲜战场,由于橡胶的短缺,我军后勤补给捉襟见肘,志愿军将士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中作战,很多甚至连一双胶鞋也穿不上,还不得不同皮衣大靴裹得严严实实的“联合国军”作战。橡胶的短缺,已成为新中国领导人心头的隐痛。扩大橡胶种植已刻不容缓!然而,现实却是让人无比尴尬: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有人的地方种不出橡胶,稍有条件能种植橡胶的云南等少数边疆地区却人烟稀少。为此,中共中央专门开会讨论这一问题。诗人气质的毛泽东听完汇报,略加思索,便在植物学家蔡希陶送呈的报告上挥笔写下:“我家乡人很多,可以调一批人去支边,开发边疆。”
一次在新中国人口迁移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大规模移民,始于一代伟人这大笔一挥。从1952年起,3万余以湖南祁东、醴陵两地青年农民为主体的浩荡大军,告别世代居住的田园,或夫妻成对,或携家带口,跪别父母,惜别亲人,千里跃进彩云之南,散布在云南3000余公里的边境线上的42个农场。从此,彩云之南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也成为他们播种梦想和希望的精神家园。
知道有这么一支特殊的支边大军,是在我的孩提时代。那时,我所在一座湘南小村庄,几乎家家都有亲戚从云南回来探亲,其中就包括我的一位堂伯父。他们是工人,却晒得比老家农民还黑,衣着打扮一点也看不出比老家人讲究到哪里去。再后来,我知道我的父母也差点成了这支支边大军中的一员,父亲母亲也曾自发追寻第一批支边大军的脚步到了云南,我的一位兄长就出生在那片红土地上。只是后来由于政策的调整,自发流入的这批人员又都回到了湖南。
因了这种种的机缘,我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整理这段历史,这段当年波澜壮阔的史实开始渐渐清晰地闪现在我的脑海,这批湖南人的创业故事也常常吸引着我、打动着我。
最终决定动手为他们写下这段历史,是一批远在云南打拼的战友及同乡的鼓励与催促。他们追逐着前辈的脚步,来到云南创业,创造了非凡的业绩。他们明白,没有当年湖南前辈开疆拓土,就不会今天云南垦区的欣欣向荣,也不会有他们今天的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对先行者一路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创造精神,心中充满敬畏和景仰。
2011年10月,我们开始一路驱车前行,奔驰在云南各垦区的采访路上。一路上,汽车音响流淌着悠远的歌声:彩云之南,我心的方向……记得那时的天多湛蓝,你的眼里闪着温柔的阳光,这世界变幻无常,如今你又在何方……
是的,我们的支边亲人,如今你们又在何方?
我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埋骨胶林,许多人正在渐渐老去。就在我第一次采访归来不久,与我在云南匆匆见过一面的伯母就悄然离世了。而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我的父母亲,也于几年前相继离我们而去。云南山高路长,采访之途充满艰辛,但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催促着我们一路前行。
半个多世纪了,那些风烛残年的支边老人还是那么乡音未改。当听说家乡来人整理他们的故事,当他们说起远去岁月的艰辛,大多难掩内心的激动,许多人甚至流下泪来。那些幸福生活着,或已经离我们而去的人,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或许压根就没想过要载入青史、流芳百世,就像当初携妻带子远离故土、要为新中国种出“争气胶”一样,他们的理想简单而又崇高。他们中的一些人,今天的生活仍不十分富足,许多人还因当年的体力透支而百病缠身,甚至在晚年还正在经历一场农垦深度改革的阵痛,但他们说起过去,一点也不为当初的选择而懊悔。随着采访的深入和故事的积累,那些已逝去的岁月和创业者的悲壮故事又活生生地跃然在我们眼前,使得我们不得不收回或许已经投向世俗的目光,甚至停下我们迈向浑浊喧嚣的脚步,凝神虔诚地将自己融入到那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中去,去感受一代人为国家使命而迸发的力量和激情。他们身上散发出的那种久违的精神,其实是这个社会进步的基因。仅凭这一点,我们就有理由记住他们。
只是,不是每一段历史都能回复到昔日的光华闪耀,不是每一个细节都能打磨到水润光鲜。尽管我们以蒙荫受宠的感恩心态,全心全意去做好每个环节的工作,但要重现支边人的光芒与沧桑,的确不容易,除了我们的水平所限,还因为支边老人中一些关键人士已经故去、或因身体原因不能接受采访,而旧有的历史资料由于年代的久远,大都是一堆枯燥的数字或概括性的记叙。即便是片鳞半爪,但当我们重温他们的故事,若为他们的命运流过泪,就不能说不认识;若为他们的的遭遇叹息过,就不能说不知道。
纸是有感情的,书是有灵魂的。拙笨的笔也许永远无法复原当年湖南支边人或雄壮、或婉约、或高昂、或沉浑的创业篇章,但你一定可以感受到一个湖南后辈无尽的谦卑和虔诚的礼拜。
曲终人不散,把酒话沧桑,惟有高山仰止,诚恐诚惶。
壬辰岁中于长沙马栏山煮酒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