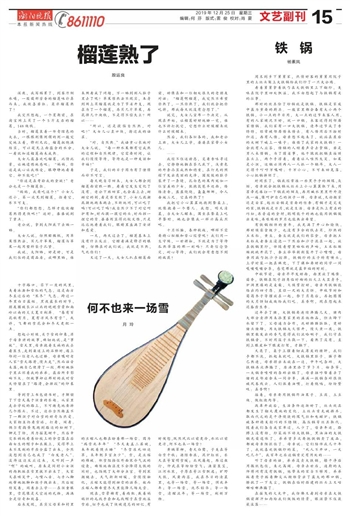周末到乡下舅舅家,热情好客的舅舅用院子里的土灶头架上大铁锅给我们炒了一只大公鸡。
看着舅舅拿着铁勺在大铁锅里上下翻炒,美味在院子里四处飘溢,我不由想起了与铁锅有关的往事。
那时的炊具除了砂锅就是铁锅。铁锅是家庭中最为重要的厨具。一般家里都会备有大小两个铁锅,小一点的平日用,大一点的过节来客人用,有的人家境况不好,就一口锅,来客还得到邻居家借锅。我们家有一口大铁锅,逢年过节成了香饽饽,经常被邻居借来借去。有人借用后不按时归还,再有人借,母亲想不起来了,就站在屋后的大树下喊上一嗓子:谁借了我家的大铁锅?一会就有人应答,借锅的人顺着声音去拿锅,若是男人来借锅,为了图省事,他干脆就把锅直接顶在头上,两个手撑着,看着让人哑然失笑。如果是小孩,这锅必须两人一人抓一个锅耳,大人一定得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小心,不可来回晃荡,小心把锅摔坏了。
时间长了,锅底经常挂一些黑乎乎的烟煤、灰垢,母亲就会把铁锅从灶头上小心翼翼取下来,用苕帚疙瘩扫一下锅底的烟灰,再用碱水里里外外清洗一遍,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母亲说,无论搬家还是安家,起灶安锅是首要的任务,有锅才是完美的家,铁锅就是日月,就是生活。母亲是队上有名的巧妇,再普通的食材,聪明能干的她也能用铁锅做出美味,再艰难的岁月也能熬出希望。
有铁锅相伴的童年,我充满了开心和愉快。那时候零食极少,也没有多余的钱去买,炒熟的玉米粒、黄豆、蚕豆就是我们的零食。母亲把玉米粒或者蚕豆浸泡一下然后和沙子混在一起,放在铁锅里炒,伴随着劈里啪啦的声响,玉米粒蹦蹦跳跳开花了,蚕豆毕毕剥剥裂开了小嘴嘴,母亲用漏勺把沙子控掉,铁锅炒的豆子特有嚼头,上学时装一把在裤兜,下了课和要好的同学一同嘎嘣嘎嘣分享,感觉那就是最幸福的时刻。
中秋节前,母亲早早发好面,面里放了鸡蛋、茴香,铁锅在院子拐角临时砌的灶火上大显身手,炉洞里填的是麦柴,火候掌控好,母亲用铁锅能烙出约四寸厚、直径一尺的大月饼。中秋节时和葡萄枣子等摆放在一起,祭了月亮后,再把圆圆的大月饼切成块给我们吃。真香啊,现在想起来还唇齿生香。
过年杀了猪,大铁锅要连续沸腾几天。猪肉大部分卖掉用来添置家里的其他物品,但头蹄下水留下了。父母通力合作,洗好肠肠肚肚,烫好猪头猪蹄,用大铁锅大火催开,慢火煮一夜,铁锅里散发出的香气惹得我们流哈喇子。我们守在铁锅旁,不时用筷子头戳一下,看熟了没有,直到上眼皮和下眼皮打架,才躺下。
天亮了,桌子上摆着切成薄皮的猪肝,我们手都不洗,抓起来就吃。大铁锅里肚子、肠子都已熟透,母亲捞出来放在一边,中午吃杂碎。大铁锅再次沸腾了,原汤里添了萝卜片、粉条等,一大锅香喷喷的杂碎出锅了,母亲招呼帮着杀了猪的左邻右舍来一同分享,满满一铁锅杂碎很快被风卷残云。人们抹着油嘴,打着饱嗝,纷纷赞叹:真香啊!
接着,母亲要用铁锅炸油果子、豆腐、土豆块、做红烧肉等。
改革开放后,生活条件逐渐好了,灶头炊具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土灶头首先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干净便捷的煤气灶和电磁炉;铁锅被各种精美轻巧的不锈钢、高压锅等灶具取代。随着我们各自成家单过,人少了,母亲年迈,胳膊上没有劲,炒菜端不动大铁锅,黑油油的大铁锅光荣退休了,弟弟曾多次要把铁锅卖了废品,都被母亲阻拦住了。母亲说:它们陪伴我几十年了,我就喜欢铁锅炒的菜,“死人不开口,一天吃几斗”,我百年之后这锅肯定有用处的……
听了母亲的话,弟弟没卖大铁锅,擦干净后用报纸包住,束之高阁。母亲去世后,造厨的大师傅问有没有铁锅,他带来的家当不够用。弟弟踩着凳子踮着脚尖从橱柜拿出了最大的那口锅,擦拭了一下灰尘,铁锅在临时搭建的灶头上又咕嘟咕嘟沸腾了。
在摇曳的火光中,我仿佛又看到母亲在大铁锅前挥汗如雨给我们做饭的情景,眼泪禁不住簌簌滚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