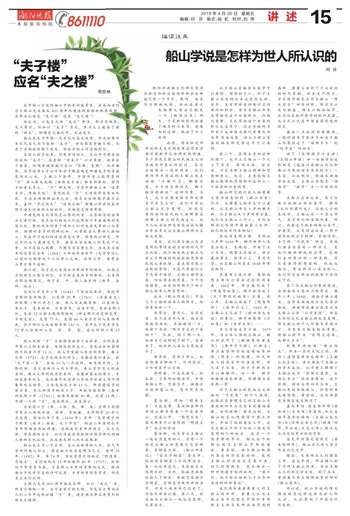我市精心打造的湘江中的东洲岛景区,在岛南为纪念王船山先生诞辰400周年而建造的高楼和配套庭园,其命名应该是“夫子楼”还是“夫之楼”?
我认为,以先生之讳“夫之”命名,则名实相符,无可厚非;但如以“夫子”名之,虽名义上拔高了楼的“档次”,但确是无据之作,无益先生。
船山先生乃中国一代文化之集大成者,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人而不能称“夫子”,并非因其资格不够,而在于清朝政府囿于政见,审批手续工作没做到位。
在国人的习俗里,对有学问的人,交往中习惯在姓别后加“夫子”,或直称“老夫子”以示尊敬,说者出于善意,知趣者诚惶诚恐答以“岂敢、岂敢”。此非谦辞,实乃读书士子必守本分不敢逾越先师诸夫子的虔诚崇拜之心也。上溯二千余年,中国历史上能得皇封“子”者入祭大成殿(俗称夫子庙)和专祠祭祀、荫封子孙者无多人,“子”即先师,学宫外牌楼上书“道贯古今,德配天地”,意思就是“子”之功德泽惠有如天地。杰出如周敦颐谥号元公,意是宋后新儒学诸子之首,嘉封“学达性天”“道南正脉”御匾以彰其代表的理学通天达地的正统地位,历朝史志煌煌有载。
中国先时文化传承是以祭祀列首、次在教育的读书方式进行的,这是我们的先人们延绵数千年最高明的亮丽之处。祭祀的目的在于增加人们对先圣先贤的心仪崇拜,增强对圣学的精神认知,从尊敬圣人事功人品切入,然后学习他们的道德思想文章,修养践行终生。所以历代文人最讲究气节,教育本旨在做人尽负天下之责,而不是钻入钱眼、只图自家富贵之乐。这也是石鼓书院宋景定五年(1264)工部尚书汤汉作《先贤堂记》,以官府仪规祭祀十六位贤人之始、后有七贤、再有后七贤之尊不逾矩。
唐以前,孔子是元圣周公旦祭祠中的陪祀。从唐太宗到唐玄宗数次封孔,孔子称至圣而专祠祭祀。元圣周公则逐渐居次,传于东、中、西三庙专祠(曲阜、洛阳、岐山)。
自宋仁宗庆历4年(1044)下旨始设县学,各地学宫祭祀逐渐规范。以乾隆25年(1760)《清泉县志》和乾隆《衡州府志》载,能入大成殿享祭,以皇封至圣孔子、复圣颜回、宗圣曾参、述圣子思、亚圣孟轲5位,先哲12位配正殿两侧陪祀(神主牌位还是称先贤,不称先哲)、先贤77人、先儒46人者方可列入东西两庑,合计神位入大成殿享祭140人。其中孔子及其学生72贤人分别列入圣、哲、贤、儒,后之所封只有67人。
能入祀称“子”又能隆显垂誉于后世者,必须是其中贤以上的杰出者,由朝廷授封先人,惠及后世世袭荫封子孙者只有11人。而入学宫敬入崇圣祠享祭,雍正元年(1723)孔子先祖五代封王,后裔世袭衍圣公,称“天下第一家”。其他10人一旦受封,故里设专祠,立祭祀田,其父母神位入祀乡贤祠,再入学宫另立的启圣祠,雍正元年间改名崇圣祠。后裔世袭五经博士,专祠选袭奉祀生,选后裔中优秀者入当地学宫读义学作预备奉祀生培养。上述包括孔子共11人,即创建儒学的前五圣,创立新儒学的宋六子。年拨官银助祭(各专祠乾隆六年(1741))始每年拨银40两,此前12两)。可谓一人封“子”,惠先泽后,直至清亡。
自宋封六子(周、二程、张、邵、朱)至明只封理学有名人物胡安国、张栻、吕祖谦、王阳明等20余人为先儒,顺治元年下旨(1644年)重申“先贤周子祀于厥里(故乡)庙庭、天下学宫”。顺治二年再封孔子重申明确其传统待遇,清朝政府重申封周子、孔子之举,旨在团结士子、公示清政府尊敬新旧儒学两位领袖人物的文化认同,此后再无封入祀大成殿者。
船山先生乃一代宗师,宋以后难得的人杰,其气节学问均高山仰止,因在他以反清复明为己志,康熙31年(1692)卒,寿74岁。清廷官员定性他是“明遗臣,清逸士”。直到他死后15年的康熙46年(1707),经张仕可等官员力推,才皇封入乡贤祠享祭祀之礼,圆湖湘士子经年不息的呼吁之愿。乡贤祠虽同在学宫,但是另立次位之祠。
王船山先生400周年诞辰在即。如以“夫之”名,则名实相配一体,自可垂誉千秋无憾,而先生之事功在人们心目中远胜如诸“子”者,遵史循实命名更有利弘扬先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