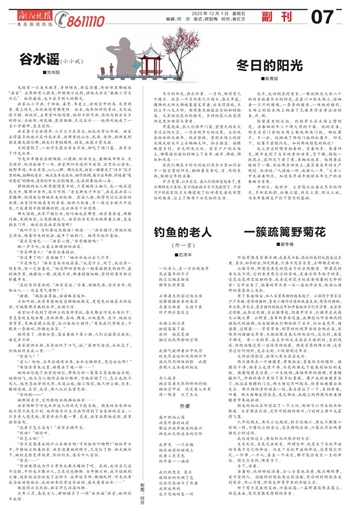■刘向阳
龙城有一位美术教员,身材颀长,面容清癯,街坊邻里都喊他“画家”。业界鲜有人提及,即便偶尔谈到,讲他无非是“教教小学生而已”。他很谦逊,也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画家从小习画,于田地、桌凳、书皮上,涂鸦空中的鸟、水里的鱼、檐上的瓦,渐渐画得有模有样。后来,他参加师院考试,文化成绩不错。面试时,主考官叫他唱歌,他却斗胆作画,很快勾勒出家乡的特征:石板街,砖瓦墙,屋顶栖猫,天边流云……他顺利地成了一名小学教师,直至退休。
画家妻子去世得早,儿子又不在身边,他就经常往外跑。画家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呼龙水库,画那里的山水、民居、老街,拍照发到朋友圈或微信群,朋友们争相围观、转发,收获点赞无数。
又到暑假了,一些学生慕名前来学画,却吃了闭门羹。画家去了呼龙水库。
呼龙水库镶嵌在耕烟镇,以灌溉、防洪为主,兼顾城市供水、生态保护、休闲旅游于一体。画家照例住进怀乡旅馆,这里依山傍水,视野开阔,井水煮茶,沁人心脾。那次采风,画家一眼瞥见了“怀乡”院子里的她,抬脚就进去。她正在井边汲水,动作协调,看不出年龄,伴随着“嘎吱嘎吱”的脆响,清亮的井水流到桶里,也温润着他的心房。
耕烟镇的女人鲜有戴帽裹巾的,只有她特立独行,包一块深蓝色头巾,像那口老井,深不可测。“老夫聊发少年狂”,画笔在画家心里腾挪,悄悄地勾勒她优美的轮廓。夜深人静,揣摩凭记忆涂抹的画像,画家惊叹她柔美的身姿,她的头低垂,另一面完全被头巾遮住,只能看到半张模糊的脸,这让画家十分遗憾。
那天傍晚,画家下楼打水,恰巧她也在那里。她穿着普通,两眼闪躲,见到画家,立马提桶走人。画家的目光任由她牵着上楼,直至挡在门外。她就住在画家隔壁啊!
“她叫什么?为何要遮住脸面?难道……”画家暗忖,待她忙碌完毕后,借着停电的机会,敲开了她的门。她愕然地盯着他。
“莫非是哑巴……”画家心想,“你有蜡烛吗?”
她一声不吭,从桌上取蜡烛给画家。
“你是哪里人?”画家试着搭讪。
“你没事了吧?我要睡了!”她冷冷地吐出几个字。
“不是哑巴!”画家没来由地窃喜,“也没什么,对了,我送你一样东西,你一定会喜欢。”他迅即回房取出一幅装裱精良的画作,塞到她手里。她瞟他一眼,犹豫片刻,捧着镜框细瞅,紧拧的眉目渐次舒展开来。
“没经你同意画的。”画家笑道,“你看,湖湘民居,清凉老井,优雅女人……你真有气质啊!”
“谢谢。”她轻启薄唇,话语略显缓和。
不知咋的,画家希望她发自肺腑地微笑,更想见识她真正的容颜,可她像那清澈的水井,波澜不惊。
画家似乎找到了精神上的某种寄托,每天都去呼龙水库打卡,有灵感就支起画架,涂抹游廊、岛屿、鸥鸟,兴味盎然。是日,他欲泛舟赏景,见她在堤上张望,就兴奋地打招呼:“看来我们有缘分,干脆共一条船吧,价格也合算。”
她同意了。湖面如墨,荡漾着数十条小船,人们边摇桨边泼水,嬉笑声不断。
画家凝视水面,长长地叹了口气,说:“桑田化沧海,谷水没了,但她始终在我心里……”
“你爱人?”
“爱人?哈哈,当年拦堤修水库,谷水全镇移民,思念永远啊!”
“难怪你常来这里,好像丢了魂一样……”
她的话勾起了画家的回忆,那难忘的一幕幕又在他脑海浮现。细雨纷飞,他与恋人相约去拍订婚照,可她家锁了门,怎么也找不见人。他焦急地等到天黑,水漫山坡,船工催促,他只好上船,坐车,辗转进城、求学、成家,两人从此未曾见面。
“你的脸——”
她侧转身子,突然撩起水珠洒向画家……
画家陶醉于呼龙水库迷人的风光不能自拔,朋友的来电却让他不得不改变计划。他所绘系列生态画作得到了省美协的关注,一位负责人想见他,商量举办个展一事。是夜,画家来跟她道别,屋里烛影摇曳。
“这屋子怎么没电?”画家去摸开关。
“别动!”她惊叫。
“你怎么啦?”
“你不是想看我的庐山真面目吗?可别把你吓跑啊!”她松开头巾,平静地注视着画家。画家迎着她的眸子,兀自红了脸。烛光映衬下,她的左脸色泽枯黄,形似朽木,委实叫人害怕。
“你是——”
“你该晓得我为什么有电也要点蜡烛了吧。是的,我怕自己这半边脸,平时也不敢示人,总是遮遮掩掩。当年搬迁时,我不慎跌到火塘,送医救治后就成了这样子。我命运多舛,婚姻坎坷。呼龙水库成为旅游胜地后,我就回来经营这家旅馆,每天看看谷水……”
她显得云淡风轻,画家早已泪湿双眸。
次年三月,春色宜人,耕烟镇多了一间“谷水谣”画室,毗邻怀乡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