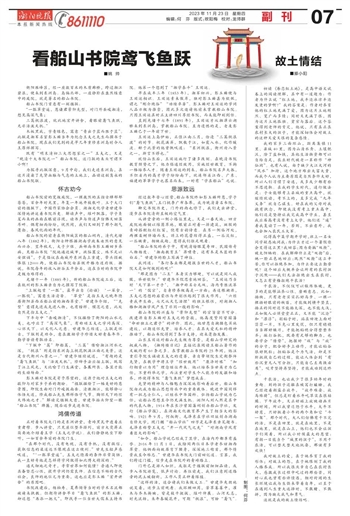■姚 帅
衡阳雁峰区,经一座数百米的木质廊桥,跨过湘江碧浪,便来到东洲岛。岛偏北部,一座静卧在盎然绿意中的庭院,就是著名的船山书院。
船山书院门首悬有一副楹联:
“一瓢草堂遥,愿诸君景仰先型,对门外岳峻湘清,想见高深气象;
三篙桃浪渡,就此地宏开讲舍,看眼前鸢飞鱼跃,无非活泼天机。”
木板黑底,字青绿色,寓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此联是湘军名宦彭玉麟当年为纪念王夫之先生而撰书于船山书院,现在我们见到的是早几年重修东洲岛时今人王厚祥挥写。
既有“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王夫之,又是“晚清十大书院之一”船山书院,这门联的来头可谓不小啊!
为探寻此联深意,9月中旬,我们走进东洲岛,在这片浸染了先贤血脉与气息的土地上,品读这副隽永的船山书院联。
怀古劝今
船山书院前的宽敞庭院,一棵巍然的五指古樟郁郁苍苍,百余年时光里,年复一年地开枝散叶。立于大门前的楹联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湘文化学者甘建华深情地讲述着书院历史。解读声中,绿叶飘落,学子负笈而来的画面在眼前浮现,读书声与传道声仿佛又回荡耳畔。偶有细雨纷纷,恍然间,我们又回到了那个朝气蓬勃、春风化雨的年代。
船山书院的前身在衡阳城区的船山祠内,清代光绪八年(1882年),衡阳士绅根据湖南学政朱逌然的意见而兴办。翌年秋天,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彭玉麟回乡养病,见船山书院“院地逼近城市,湫隘嚣尘,殊不足以安弦诵”,于是倡议在南城外东洲岛上重建,带头捐献俸银12000两,使船山书院由县级升格为道府级。据说,书院每年的收入折谷五千余石,这在当时的书院中是极为难得的。
光绪十一年(1885年),新的船山书院竣工后,远在杭州的彭玉麟亲自为之撰写了院联。
“上联起首‘一瓢’,最早出自《论语》‘一箪食,一瓢饮’,寓意生活清苦。‘草堂’是指王夫之晚年隐居衡阳县西石船山前的湘西草堂。”甘建华介绍,“‘先型’意谓先进或先进人物,也有榜样、模范之意,此处自然是指王夫之。”
下半句中“岳峻湘清”,不仅描绘了衡阳的山水之美,也呼应了“高深气象”,有称颂王夫之学问高深、心怀天下、以文化人之意。甘建华总结道,上联是怀古,下联则是劝今,意在激励学子珍惜大好青春年华,勤学苦读考取功名。
“下联中‘篙’即船篙,‘三篙’借喻湘江河水之深,‘桃浪’则是指东洲岛上桃花飘满江面之美景,这是古代衡州八景之一。”甘建华继续说道,“有趣的是‘鸢飞鱼跃’与‘活泼天机’,修辞手法应接上联,既写了江上风光,又比喻了门生满堂,各展所长、各显才能的生动场面。”
彭玉麟对书院是寄予厚望的,这源于他对王夫之的敬仰与对家乡子弟的期盼。“楹联描绘了一幅美好的愿景图,即院生面对门外峻拔南岳、清澈湘江,能够静心体悟大道,修成船山先生那样恪守气节、胸怀天下的经天纬地之才。”解读完楹联大意,甘建华抬头仰望一眼“船山书院”牌匾,随后迈步走进书院。
鸿儒传道
正对着书院大门的是东洲讲堂,青砖黑瓦中透着庄重肃穆。步入讲堂,只见座位整齐排列,前方大荧屏正简要地介绍着王学(王夫之学说)。我们静静地坐下聆听,一如百余年前的书院门生。
“在那个时代,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没有微信,获取信息的渠道远不像现在这么便利。”甘先生轻声感叹道,“‘一瓢草堂遥’,王夫之隐居的条件非常简陋,我一直好奇他是怎样将学问做得如此博大精深的。”
通天彻地之奇才,寻常世界如何能懂?普通人即使具备坚忍心性,提升学问仍需良师。在信息不畅的古代社会,良师的地位尤为重要,这也应是彭玉麟“宏开讲舍”的原因吧。
书院改建后,杨柏寿、夏彝恂等当时的学术名流都被请来执教。但期待讲舍早日“鸢飞鱼跃”的彭玉麟,却还想“再添一把火”,即找寻一位当世大儒来主持书院。他第一个想到了“湘学泰斗”王闿运。
早在咸丰三年(1853年),湘军初兴,彭玉麟便与王闿运相识。王闿运素来傲岸,独对彭玉麟甚为钦佩,谓之“刚介绝俗”“功绩卓著”。彭玉麟对王闿运的学问人品亦极为推崇,因此多次邀请他前来掌教船山书院。只因王闿运其时正主讲四川尊经书院,而未能即刻到任。
直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王闿运才从湘潭云湖桥来到东洲岛,掌教船山书院。至为遗憾的是,老友彭玉麟已于一年前下世。
王闿运上岛伊始,正值江南三月,恰逢“三篙桃浪渡”的时节。桃花满岸,飘散于江,如霞入水,化作暖波。醉于此景的他曾慨叹道:“东洲桃浪,衡州府八景之一,斯言不谬也。”
就任山长后,王闿运施行了诸多改制。在晚清书院教育颓势之下,他力倡通经致用,实施经世教育,不拘一格培养人才。随着王闿运的到来,船山书院名声大振,不但省内的高才学子纷纷南下,就连邻省江西、广东、福建的莘莘学子也慕名而来,一时有“学在船山”之说。
思源致远
经过数年苦心经营,船山书院终如彭玉麟所愿,学子们“鸢飞鱼跃”,王门桃李广布各界,成为晚清著名书院。
聊完书院历史,门外的雨也停了,我们走出讲堂,漫步在书院清新至极的空气里。
从讲堂旁的一侧小路往里走,又是一番天地,四方庭院地面铺以绿茵草地,眼前正对着一排建筑,斑驳的青砖搭配红栏红窗,饶有古韵诗意。在另一侧临河处,两棵栾树伴墙而生,顶上的花蕾结得正盛,一丛淡红,一丛嫩黄,相映成趣,惹得我们驻足观看。
“船山书院的弟子中,有晚清榜眼夏寿田、民国传奇人物杨度、‘湘南教育王’蒋啸青,还有本是木匠的齐白石。”甘建华的脸上写满了神往。
我问道:“各行各业都是超拔当世的人才,船山书院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那是因为‘二王’本身实力够硬,可以说是同人咸服,举世钦仰。”甘建华不假思索地回答,“王闿运乃当时‘天下第一才子’,‘湘中称名士无双,海内号胜流第一’的‘儒宗’,自身修养极高是一方面;再追根溯源,王夫之思想的启蒙性与开创性起到了很大作用,‘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独立根性,对湖湘人格和湖湘学风产生了非同一般的影响。”
船山书院的兴盛与“景仰先型”的宗旨密不可分。改建源自彭玉麟对王夫之的崇敬,他高度赞同曾国藩“命世独立之君子”的评价。因此,他甘愿自掏腰包买地建校,以期追怀先贤、培养人才。在其大爱无私的精神推动下,船山书院得到了各方支持,迎来蓬勃发展。
山长王闿运对船山先生极为尊崇,是船山学研究的权威人物,《湘绮楼日记》直接记录阅读王船山著作的文献约有60条之多。在掌教船山书院的25年间,他注重引导院生诵读王夫之的遗著,亲自带领院生定期祭拜先贤,在教学中将王学“经世致用”“康济时艰”“知行相资以为用”理念继往开来。他以培养当世英才为己任,不重科举之学,而注重对学生个人能力的发掘和培养,终使得书院“鸢飞鱼跃”梦想成真。
先贤的精神与人格魅力深深地影响着后世,船山书院由此成为船山思想传承中的重要载体。晚近中国同样有一批志士仁人,以继承中华国粹、弘扬船山学说为己任,让船山思想至今仍充满生机。浏阳人刘人熙是其中的代表人物,1914年在长沙曾国藩祠创办船山学社,发行《船山学报》,在湖南文化教育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921年9月,何叔衡、毛泽东在学社旧址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现门楣“船山学社”四字是毛泽东亲笔题书。毛泽东称赞王夫之“开一代风气之先”“对湖南学风有着巨大的影响”。
“如今,船山学说已经成了显学,在海内外都享有盛誉。2016年11月1日,我陪同两位日本学者参访湘西草堂。他俩面向故居弯下腰身,深深地三稽首,那个情景我至今难忘。”甘建华在书院大门前回忆道。言罢,我们跨过门槛,信步走在书院外的青砖路上。
门外已是游人如织,或驻足于楹联前细细品读,或步入书院游览,低声讨论。再往前走,我们注意到道路旁的泥土被翻新,工作人员正种着绿植。
“这样的活,适合请我们来做义工。”甘建华爽朗地说笑着,迈步上前观看。我环顾四周,芳草萋萋中,灌木与乔木掩映,皆是枝干挺拔、绿叶伸展。山河无恙,时光流转,来年春暖花开,可期“桃浪”,可盼“鸢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