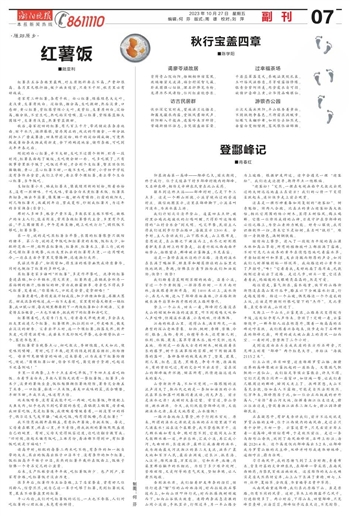■陆亚利
红薯在五谷杂粮里最贱,对土质肥料要求不高,产量却很高。春月里无根扦插,极少病虫侵害,只要不干坏,秋月里必有好收成。
老家有三种红薯,各有千秋。白心红薯,绿藤绿色大尖叶,皮浅黄,生薯质纯白。淀粉低,糖分高,生吃微甜,熟后淡黄,口感甜。黄心红薯,紫红藤紫绿小尖叶,皮紫红,生薯质奶白,淀粉高,糖分低,不宜生吃,熟吃粘实噎喉。蓝心红薯,紫绿藤蓝脉大圆绿叶,生薯质浅蓝,熟薯紫蓝微甜。
秋后,每家挖回的红薯,有几百上千斤,带泥铺放在杂房地面。晾干水汽,摘掉藤根,留存周正的,残次的作猪食。一部分挑到加工厂磨成薯渣,回来榨滤淀粉。晒干的淀粉调成糊,可烫熟做成薯粉条或摊成荷折皮。余下的码进地窖,储作杂粮,可吃到次年开春之后。
刚挖的白心红薯,并不太甜,生吃不过图个新鲜。贮存一段时间,红薯表面起了皱纹,生吃便会甜一些。吃多吃腻了,只有做事劳累肚子饿了,吃饭还早时,才会削个生红薯,暂且顶住饥肠辘辘。黄心、蓝心红薯不甜,一般不生吃。那时,小学初中学校没有条件办食堂,我们上学时,要么带个煨红薯,要么带个生白心红薯,当午饭吃。
生切红薯小片,晒成红薯米,像裁缝用剩的划粉,附着些粉末,没有一丝甜味。干吃无味,常凑合白米煮红薯米饭。红薯蒸熟切条,晒出牛筋薯,像果脯一般,甜而有嚼劲。打霜的秋阳天,刮几场红薯片,收藏到年边,剪成菱形,炒制成红薯片,为过年的当家换杂(零食)。
那时人多田多,粮食产量不高,多数农家主粮不够吃。缺粮户的女主人们,能省则省,常用杂粮红薯替代主食。乡里有个民谣,“早上圆猪圆羊,中午芝麻裹糖,晚上吹吹打打”,调侃饭不够吃,红薯当餐。
第一句,说的是吃蒸红薯当早餐,长圆的红薯像整只微缩的猪羊。第二句,说的是中饭吃加红薯煮的米饭,饭粒太少,如配料芝麻一样,粘附在红薯块、红薯丝、红薯米上。第三句,说的是吃煨红薯当晚餐,从灶灰里扒出的红薯有点烫,一边用嘴吹冷,一边在左右手掌里交替腾挪,迅速拍打灰烬。
民谣流传甚广,妇孺皆知,将生活的艰苦幽默成诗意奢华,同时也概括了红薯的多种吃法。
蒸红薯老家乡语叫“炘红薯”,多是作早餐吃。洗净的红薯叠进鼎锅,加小半锅水,慢火蒸煮。红薯熟透,鼎锅底会积存一层粘稠的糖汁,饴糖似的甜,常由我独霸独享。母亲巴不得我多吃红薯,笑着说:“你箇徕几,口就是金贵,爱贪甜咯!”
红薯煮着吃,要削皮滚刀切成段,加少许猪油和盐,再撒点葱花。甜咸混杂的味道,我一向不太喜欢。家里有时每天都煮一锅红薯,我口腻心烦,每次碗里都要剩下一两块红薯和小半碗汤。父亲爱惜五谷粮食,一点也不嫌弃,把我剩下的红薯和汤吃完。
红薯煨着吃,无需专门生火。母亲每天早晚煮潲,多会在大灶灰里放进几个红薯。红薯煨熟,扒拉到灶口,外皮略焦,散发出淡淡的甜香。父亲出早工时,选一个煨红薯,拍落灰烬,剥开焦皮,吃得有滋有味。我若来不及炒饭吃早餐,也会顺势扒出一个,塞进书包里。
煨红薯常当晚餐点心,初吃数次,香甜饱腹,天天如此,便觉味同嚼蜡。有时,吃了半截,趁黑悄悄走到屋后猪栏,扔给猪吃。母亲听见猪嚼食的响动,过来察看,以为我省下红薯给猪吃,便说:“箇煨红薯沁甜,你舍不得吃,箇灾猪子贪潲,吃起还不欢喜倒哒!”
乡里一日两餐,上午十点左右吃早饭,下午四点左右吃晌饭。为着节省白米,多数人家隔天就有一餐红薯饭。红薯多,白米少,淡黄的薯块垒叠,饭粒勉强糊住薯块缝隙,薯香完全掩盖了米香。一口红薯,黏连一点米饭,再夹口咸味的菜,混合嚼磨,半甜不甜,半咸不咸,味道有点怪。
纯米饭喷香,没有菜我能干吃一两碗。吃红薯饭,即便配上大鱼大肉,似乎也找不到吃荤腥的感觉。鼎锅提上锅架,母亲喊我回家吃饭,见是红薯饭,我便噘着嘴皱着眉,一副没胃口的样子,偶尔还生气发牢骚:“喊我吃饭,吗冇得饭嘞,尽是红薯!”
我不情愿地揭开鼎锅盖,有意扒开薯块,专挑米饭。每次,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并不责怪,将我挑剩的薯块默默盛进自己的碗里。有时,父母又觉得纵容过度,边吃边翻古教育我:“旧时候,挂起禾镰冇饭吃,上滩月份,斋汤都不得到口,有红薯饭吃就是万福哒!”
读高中时,标配的每餐三两米吃不饱,有条件的加一把自带的大米,蒸出的饭高出钵子口沿半寸。没有条件的加个红薯,饭粒抬高齐平钵子口沿,蒸熟的红薯半截斜在饭面上,饭钵子仿佛一个奇石突兀的小盆景。
后来,生产队粮食连年丰收,吃红薯饭渐少。包产到户,家家有余粮,吃红薯饭才淡出历史。
很多年后,红薯作为五谷杂粮,上了店家餐桌。曾有好几位同龄人,信誓旦旦,说自己这一辈子吃够了红薯,见到红薯就反胃,果真不动餐盘里的红薯。
平心而论,我们对吃红薯饭的记忆,一点也不夸张,人们对吃红薯的心理抗拒,未免有些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