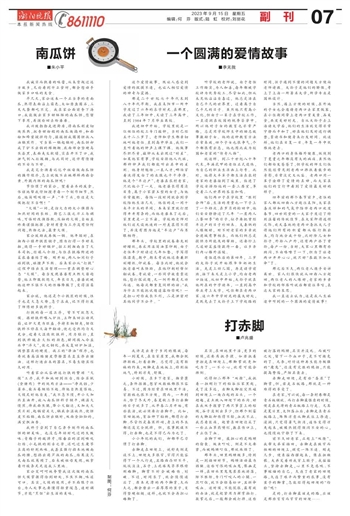■朱小平
我诚实而执着的味蕾,从未背叛过远方故乡,无论看到什么食材,都会想动手做家乡口味的美食。
早几天,家公送来一个正当季的老南瓜,熟得表面沾上霜色,大如磨盘圆石,三天九餐都吃不完。我在家公面前夸下海口:我能做出家乡甜酥酥的南瓜饼,您留下享用,再捎些回去给婆婆。
我兴致勃勃走进厨房,将南瓜削皮切块蒸熟,把香甜粉糯的南瓜块捣碎,和面粉加蜂蜜搅拌均匀,揉搓捏成圆团饼状入油锅煎炸。可当第一锅起锅时,南瓜饼却成了铲不出锅的稀糊糊。底面部分坚硬乌焦漆黑,表面夹生软塌,实在开不了口,我泄气倒入垃圾桶,与此同时,还伴有情绪的不安与不甘。
我是完全循着记忆中祖母做南瓜饼的操作程序,怎么就做不出她那样两面金黄、外脆内酥的南瓜饼呢?
节俭惯了的家公,望着丢弃的废食,体谅地帮我仔细搜寻每一个制作细节,然后,他简明叹惜一声:“平丫头,你这是火候把控不当啊!”
“火候”一词,是指火力的大小强弱与加热时间的长短。厨艺三技之刀工与调味,可临时改换搭配,压轴的火候,自始至终要谨慎把握。食材质量与工序没有任何问题,熟物之法,最重火候。
家公鼓励我再做一锅。他年轻时,在湘西小镇开铁匠铺子,因为打得一手好耒耜,烧得一手好锅炉,招工到湘南当了火车司机,经媒人介绍,与住在铁路附近的菜农婆婆结了婚。刚开始,两人如同钉子碰到铁,碰撞声不断。后来家公从“打铁”过程中悟出生活哲理——重在调整好心态“火候”。每当发现婆婆有点燃火苗趋势,他立即服软熄火。年长日久,婆婆就被他这种不愠不火的性格降服了,变得温柔起来。
家公说,他还是个小铁匠的时候,性子也是火急火燎,急于求成,记不得打废了师傅好多铁料子。
打铁的每一道工序,皆不可疏忽火候。拣好铁料喂入炉灶,立即来回拉动风箱,让炉火更为旺盛。手持长柄钳夹,钳住铁料不停在火海中翻动,使之受热均匀又充分。趁着火温烧软铁料,用力锻打,直到铁料褪去火红的颜色,瞬间投入冷盐水中“淬火”,使之钢化,再反复回炉加温,调整器具的硬度。收工的“泽油”程序,也要就着高温贴猪皮摩擦器具直至渗出猪油。这样打造出来的器具,不易生锈且经久耐用。
听着家公从容讲述打铁的繁琐“火候”工序,我平和地回到灶台,结合苏轼《食猪肉》中的炖肉方法——“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我不急不慢,开小火加热至油开,放入南瓜饼料子铺平,调温火慢煎,待底面焦脆,降小火翻边,又加大火煎片刻,起锅前关火,锅底余温收热,使饼皮不粘锅。南瓜饼出锅时,双面金灿灿的,满室飘油香。
我终于尝到了自己亲手制作的南瓜饼的甜美味,也没忘年幼时吃过的失败味:青梅子的酸掉牙、绿番茄的涩到喉咙打结、小毛桃的割舌之苦,还吃过生魔芋豆腐的针刺麻味。我甚至强行掐本地嫩南瓜的腰,想掐出葫芦状的南瓜,结果没几天南瓜就蔫殒了,后来被祖母发现,她拿着竹枝条足足追我三里地。
家公笑呵呵地夸赞我这次做的南瓜饼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不焦不糊,味道可口。其实,火候的使用,并不局限于灶台,为人处事也要懂得轻重缓急,适时调节,才能“烹饪”出生活的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