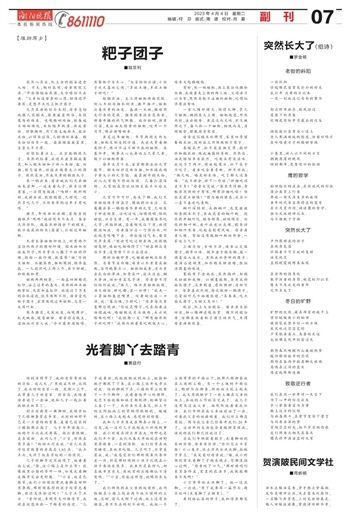■陆亚利
农历八月后,队上分的糯谷进仓入柜。不久,相对农闲,母亲催促父亲:“早些推糯谷蒸酒,天冷嗒怕不出酒。”父亲知道母亲的心思,甜酒迟早要蒸,是想早点吃上粑子团子。
九月蒸酒的时令未到,母亲急切地撮几筒糯米,提着簸箕绢筛,来到屋场的碓房。吱嘎踏响碓轴,铁舂磕头砸响碓坑,米粒随声跳荡,渐成齑粉。停歇踏碓,用丫杈支起碓木,搲出米粉,以绢筛过筛,几轮循环再舂。糯米粉似白雪一般,层层铺落簸箕里,垒叠大半寸厚。
时值红薯出土,正宜做锅烧丸子。蒸熟的红薯,放进木盆里捣成薯泥,加入糯米粉和少许八角粉、盐、白糖,搅匀揉熟,捏搓出鸡蛋大小的团子。烧热菜油,炸成焦黄的锅烧丸子。
第一锅出来,母亲喊我们兄弟姊妹来尝鲜,一边夹着丸子,昂首往嘴里塞,一边得意炫技:“吗样?配料刚好,咸甜合适,软软糯糯,几好吃。趁热多吃几个,不然要等到过年才有吃嗒。”
腊月,年味渐渐浓稠,屋场里的捣碓声“咚咚”地持续半个来月。各家次序排队,捣舂蒸甜酒余下的糯米,秋日收获的秫米(高粱),打制过年糍粑。
木质长条糍粑印版上,刻有两个直径约两寸的圆形印模。糯米粉加水揉成剂子,用手掌压入撒了干粉的印模,轻轻一敲印模,跌落带“福”字的生糍粑。木甑蒸熟,糍粑圆润,糯香氤氲。一人趁热吃上两三个,虽不甜腻,却软糯和胃。
糍粑两两相叠,一面盖四瓣梅花红印,沾上过年的喜庆。蒸熟的秫米糍粑紫红,无需加盖红印。放进过了冬至的冷水浸泡,经月保鲜不坏。母亲爱吃粑子团子,家里做的过年糍粑,总有一大荷叶缸。
寒冬腊月,天寒地冻,向晚围炉,红光映面,暖意融融。母亲径自做主,温婉地对家人说:“今日莫煮泡饭嗒,煎餐粑子当点心。”大家纷纷应诺,小孩子欢天喜地尖闹:“多放点糖,多放点糖才好吃!”
起锅添油,文火将糍粑两面煎软。倒入半碗白糖水焖煮,激干糖汁,糍粑泛着焦黄的油光。盛满一头碗,撒些预先炒香的芝麻,糖香糯香混合芝麻香,伴着升腾的热气飘散。端白粗碗,持黄竹筷,夹扯油光橙黄的糍粑,咬开一个月牙,嚼出满嘴甜香。
虽是过年糍粑,年节期间大肉大鱼,糍粑反倒受到冷遇。我成天贪着糖果饼干,绝口不沾不甜不咸的糍粑。来客拜年,晚餐点心也要端上几荤几素,极少以糍粑待客。
每年正月十五,家家都要滚些元宵散节。糯米粉拌芝麻白糖,加水揉成鸽子蛋大小的元宵馅。簸箕摊开糯米粉,放入元宵馅不停地筛动。几番打湿筛转,元宵馅滚雪球似的变成乒乓球大小。
元宵可炸可炒,尚未下锅,我们兄弟姊妹便手持筷子,围拢到灶台边。笊篱撮出第一锅糯香焦黄的元宵,几双筷子伸进碗里。边吹边咬,细嚼慢咽,酥软甜腻,口舌生津。有一年,我囫囵吞枣吃元宵,热馅挤破,沿着喉咙往下烫,痛得眼泪双流。母亲连忙舀一勺筒冷水,叫我赶急咕噜下去。待我缓过气来,母亲厉声责骂:“前世冇吃过好东西,就跟饿佬鬼样,咯副吃相吗得了!”好在那次烫伤不重,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
那时白糖珍贵,吃糖激糍粑次数有限。为着节省白糖,母亲以水煮青菜糍粑,当作晚餐点心。糍粑切成条,清水煮出乳白的浑汤,加青菜叶,放点淡盐,搁点香油,彷如青菜毛芋汤。母亲舍不得似的对我说:“徕几,咯水煮糍粑软糯,汤又糊粘,好吃嘞,尝一口啰!”我夹一小条糍粑塞进嘴里,咬着碗边汲一口汤,说:“寡淡咯,不好吃!”母亲每次重复那句现话:“你就是嘴刁,吃东西要沾油腥咸味,咯糍粑也是米做咯,未必就咯难吃啊!”我狡黠一笑:“哪有糖煎粑子好吃啰!”我转而闹着要吃剩饭点心,母亲又起锅暖饭。
有时,蒸一碗糍粑,面上象征性撒些白糖,我抢着夹上面的两三块。父母亲习以为常,默默夹起不沾糖的糍粑,吃得似乎有滋有味。
一家人围炉烤火,闲得无聊,拿几个糍粑,搁到炭火上煨。糍粑起泡,外焦内软,溢出糯香。虽是淡而无味,炉火映照之下,每人抓一个糍粑,相视而笑,清闲暖食,驱散周身寒意。
母亲迷信糯米补脾胃,家里四季留备糯米粉,随时派上用场做粑子团子。
春暖花开,扯半箢箕嫩艾草,捣碎拌和糯米粉,做成扁圆的青粑。蒸熟后,油光暗绿草香浓烈,吃起来有苦涩味。我咬不了两口,便皱起眉头,扔下筷子不吃了。母亲咬含着青粑,好言劝我:“徕几呃,咯是好东西,吃了解火清毒咯。”我不理会,摔下一句话:“拌糖吃还差不多!”母亲大笑说:“屋里冇得糖,青粑苦阴阴的才有味,哪有拌糖吃咯?你就是爱点甜咯!”因为糖的诱惑,我自小一直不喜欢吃青粑。
桐叶深绿时,采撷桐叶,包裹揉搓短条糯米剂子,蒸成瓷青的桐叶粑。趁热剥开桐叶吃,糯香醇厚,回味绵长。冷结的桐叶粑,连叶放进灶灰煨,糯香拌和桐叶焦香,吃起来别有风味。母亲看重人缘,常给没有做桐叶粑的邻舍,一家送上几个。
上滩月份,百味不济,母亲必定做团子,调节口味。搅半盆子糯米糊,搲一调羹汆入滚水,煮熟成水蛋样的团子。连汤舀进碗里,加些糯米甜酒糟,胜似汤圆羹的味道。
夏秋有了老南瓜,蒸熟捣碎,加糯米粉揉和成糊。以调羹搲取,汆煮成的南瓜团子,淡黄剔透,慈软微甜,清新可口。母亲喜欢热闹,每次做好一锅团子,总爱招呼几个姑嫂侄媳:“来来来,吃点南瓜团子,又甜又爽口!”
秋后,队上又分糯谷。母亲亲自挑回家,细心腾挪进跶柜里。燥烈的糯谷香,仿佛裹挟着粑子团子的热气,熏得母亲满面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