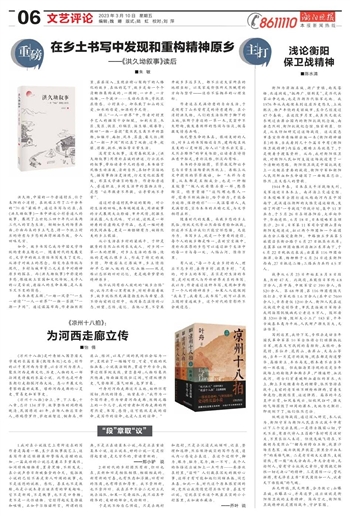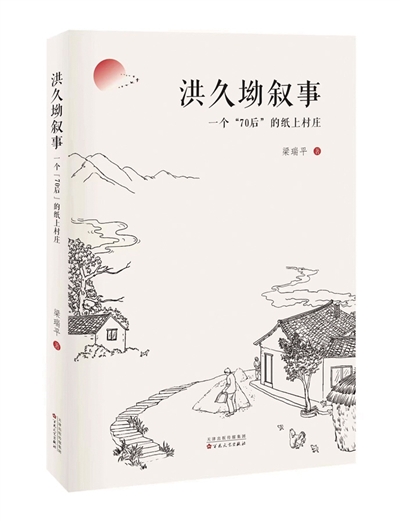■朱 敏
洪久坳,中国的一个普通村庄,位于耒阳的小湾村。在纸媒工作了二十余年的“70后”梁瑞平,通过书写与记录,在《洪久坳叙事》一书中讲述小村普通人的故事,展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两三代人的百态生活。栩栩如生的场景画面,扑面而来的乡土气息,将一个纸上村庄的诗意与乡愁刻画得淋漓尽致,令人回味无穷。
如今,故乡书写已成为中国文学传统的重要主题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文学中的故土情结书写发生了变化,从游子对故土的思念,转变为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等二元关系中对精神原乡的探求。而《洪久坳叙事》中弥漫的乡愁,根植故土家园和文化传统,关乎人的心灵安放,连接人的生命来路,是人类不灭不变的情感。
本书共有五辑:“一坳一风景”“一生一世情”“一人一世界”“一物一菩提”“一朝一夕间”。通过谋篇布局,作者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呈现出精心架构下的人格化的故乡。在他的笔下,故乡是由一个个清晰物象构成的,一棵树、一口井、一方池塘、一个渡口……生动而具体,寄托浓浓情感。小村虽小,却承载了如山的父爱、如水的母爱、如酒的手足情。
辑三“一人一世界”中,作者对村里手艺人的描写十分细腻,如剃头匠、木匠、篾匠、铁匠、补锅匠、接生娘、媒婆等;辑四“一物一菩提”聚焦民生离不开的器物,如镰刀、扁担、风车、算盘、柴火灶;辑五“一朝一夕间”则记录了双抢、过年、赶墟、撑船、挑水、晒谷等日常生活。
没有宏大叙事,没有春秋笔法,《洪久坳叙事》用质朴真诚的讲述、行云流水的叙事,带给读者平凡的感动。本书语言风格生动活泼、清新自然,真切平实接地气。描写事物活灵活现,行文变化疏落有致,彰显文学语言的魅力。作者给普通人、普通职业、乡间生活中的器物立传,是想“让卑微者不卑微,让寻常地不寻常”。
通过对普通村民命运的架构、对小村生活的回味,本书娓娓道来,用讲故事的方式展现大众脸谱、市井风情,挖掘生活底蕴、人生况味。可以说,这既是一部好看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也是一幅耐看的民间画卷,更是一曲铿锵有力、婉转优美的乡土歌谣。
从小生活在乡村的梁瑞平,于钟灵毓秀的自然山水间长大成人。对乡间一草一木的理解,对乡土生活的感悟,使他的灵魂扎根乡土,形成了特定的故乡情。即便后来迁居城市,乡土情结却早已融入他的文化血脉——既是难以忘怀的旧时记忆,更是魂牵梦萦的精神原乡。
他不认同有些人鼓吹的“故乡沦陷”论,认为只要心里有故乡,时时牵挂着故乡,故乡就依然充满蓬勃生机与希望。在不停向前的过程中,他用眷恋温情的心态,回望、总结、追忆。在他心里,不管离开故乡多远多久,都不应迷失家所在的地理坐标,以及家庭价值所天然赋有的方向与坚守——这些不容抛弃的心理坐标。
作者追求充满诗意的自由生活,于是便有了山水皆有灵的诗意建构。在小湾村洪久坳,人们的生活依附于脚下的土地,依附于身边的一草一木,荒蛮中不失野趣,散发着别样的悠闲与恬淡,极易激发情感共鸣。
他礼赞生命的本真,歌颂美好的人性,对乡土的书写贴近自然,建构起至纯至美的心灵田园,给人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审美体验,让读者在诗情画意中驻足,素朴淡雅,但淡而有味。
本书的手绘插图,寥寥数笔即让手艺与日常生活场景跃然纸上。再配上从文中提炼的寥寥数语,如“木料与老舅,从来都是互相成全,也是一种相互较量”“做人就要像石磨一样,憨厚踏实,稳重靠谱”“这陀螺也像人一样,需要不断地抽打,给予动力,才能奋力旋转,保持精彩”……或温馨动人,或充满哲思,实为本书的点睛之笔,与文字相得益彰。
随着时代的发展,承载乡愁的乡土民俗、传统文化等必然面临考验和挑战,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只能空怀愁绪,无能为力。书写乡土,就是一个重要的途径。每个人的故乡都是唯一,在时空变换中,质朴而浓厚的乡愁可以通过融于生活中的每一日与每一处,人隔山河,情传万里。
有人说,“每一个走出乡村的人,理应不忘乡村、善待乡村、敬畏乡村。”是的,对乡土的书写,其实是对生活的书写,是对处理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书写。我以为,作者通过这种书写,发现和重构了一个人的精神原乡。如果人人能做到“我来了,我看见,我书写”,就可以在纸上随时重返故乡,这个时代的背影终不会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