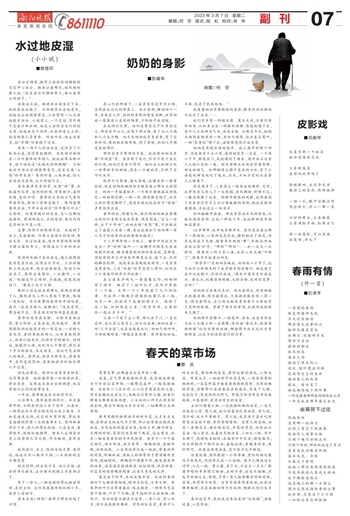■彭建华
在心灯的照耀下,一道身影穿过岁月尘烟,呈现在我记忆的屏幕上。白云苍狗,弹指四十一年,虽物是人非,奶奶的身影却愈发清晰,时常回放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场景,不断给予我温暖。
在我的记忆里,奶奶没有在生产队里出过工。那时家中七人,还喂了两头猪,养了七八只鸡和几只大洋鸭。白天里奶奶就负责家务,有了空余时间,便纳鞋底做布鞋。到了夜晚,奶奶几乎都是在纺棉纱。
那时家里只有两间半屋,我就跟奶奶住在那“半间屋”里。虽然有了电灯,尽管只是十五瓦的灯泡,奶奶还是舍不得用。她从后山枞树上砍一些带枞膏的树枝,傍在一只破碗里,点燃了当作灯来用。
枞膏灯火昏暗,每天夜晚,我醒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奶奶和她的纺车映在墙上那巨大的影子。奶奶一手摇着纺车,一手牵引着被搓成狗尾巴一样的棉花棒,一缩一伸,棉花棒变短了,纺车上的纱团变臃肿了,漫漫长夜也就在纺车“嗡嗡”声里悄然流逝。
童年的我,懵懂无知,居然将奶奶映在屋墙上的纺纱身影当成电影看。现在想来,“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奶奶出镜“电影”里,不仅给我上了启蒙人生第一课,更让我感知了奶奶那一辈人为子孙后辈付出的磨砺与酸苦!
十三岁那年的一个晚上,睡梦中的我突然发出一声“哎哟”喊叫——右脚弯内侧毫无来由地剧烈疼痛。略为懂医的奶奶检查后说,是肿毒,得赶紧到井子冲余医师那里去治,拖下去,华仔的脚会毁掉。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呀,一是家里没有余钱,二是“双抢”时节没有人帮忙,如何去三十里路外的井子冲就医?
在父母哀声叹气一筹莫展之际,奶奶却有了动作。她拿了一把竹扒子,在院子里捉了一只鸡,又用一个小布袋盛了几个焖红薯,然后用一根绳子将鸡和红薯扎在一起,双手一举,就挂在了我娘的脖子上。做好了这一切,奶奶催我父亲:“你背华仔,玉英和你一起去井子冲。”
父母一下有了主心骨,两人出了门,一直往前冲。我趴在父亲背上,回头往后看,奶奶迈着一双“三寸金莲”,也在追赶着我们。奶奶气喘吁吁,不停地嘱咐着:“那鸡是医药费。医师要就给他,不要,就卖了钱再给他。”
我看着奶奶步履踉跄的身影,眼里的泪水抑制不住流了出来……
我们家乡有一种糯米酒。夏天天热,乡亲们劳作回来,从缸里舀出一碗糯米酒糟,悠悠地喝下去,整个人立马神清气爽,痛快至极。如果是冬天,把糯米酒倒在锅里煮一煮,再加个鸡蛋,佐点姜末葱叶,一碗“色香味”喝下去,温暖便慢慢洋溢全身。
奶奶是煮糯米酒的高手。我上高中时刚十四岁,学校离家十五六里,每周回家拿一次菜。一个周六下午,刚进家门,我就闻到了酒香。揭开床头边条几上的小瓷缸一看,糯米酒糟正咕咕地冒着香醇、甜美的酒气。我哪顾得上揩干直流的口水,拿了小汤匙就肆意地吃了起来,后来,不知不觉就伏在条几上睡着了。
许是喝多了,心里涌上一股难受的燥热。突然,我梦见自己进入了一处桃园,清风拂面,舒畅不已,一激灵便醒了过来。刚睁开朦胧的双眼,我便看到了坐在旁边凳子上正打着瞌睡的奶奶,她还在摇动着蒲扇,为我送上一份清凉。
奶奶瞌睡中摇扇,那道身影溢出来的情感,比糯米酒更浓郁,让我一醉数十年,永远醉倒在幸福和温馨里。
18岁那年,我开始学骑单车。虽然在后座上绑了一根扁担,心里却还是慌乱,腰杆扭成了麻花,双手也撑成了木棍,随着单车的跳“舞”,车轮也开始在地上写“8”字。“哗啦”“哗啦”……我一次又一次摔倒。随着信心的七零八落,我在心底大喊“不骑了”,推着单车就要往回走。
“再等等!”是奶奶在喊我。奶奶快八十岁了,也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我学骑车的岔路口。她先递了毛巾让我擦汗,然后对我说:“骑车不要老是盯着龙头。看远点,就看前面的路,大胆去骑,我保你没事。去吧!”
奶奶的方法果然灵妙。因为看得远,对前面路况把握准确;因为看得远,不再拘泥眼前的一得一失;因为看得远,自己的大脑及身体各个方面就有了更好的协调。掌握了骑车的要领,我很快就能骑车上路了。
奶奶挥手岔路口,一脸慈祥。后来,这道身影成为我人生路上的一座雕像,连同着“看远点,就看前面的路”这句朴素的话语,都储攒为此生无比宝贵的财富,让我不断汲取前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