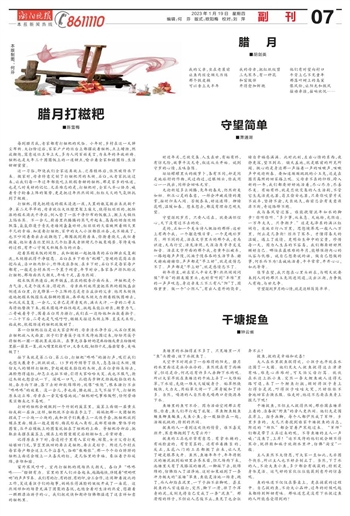■陈雪梅
每到腊月底,老家都有打糍粑的风俗。小年时,乡村在这一天掸尘布新。大扫除过后,家家户户的灶台上都摆放着糍粑,点上蜡烛,燃放鞭炮,寓意送灶王爷上天,多为人间百姓美言,为来年的丰收祈祷。糍粑也是大年三十团圆饭上的一道甜点,喻示着全家和睦团结、生活甜甜蜜蜜。
这一习俗,即使我们全家远离故土、迁居桂林后,依然被传承下来。搬家时,母亲特意定制了打糍粑用的木槌、石臼,从老家托运过来,让我们每一年过年都能吃上软糯香甜的糍粑,那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儿时美好的记忆。尤其难忘的是,打糍粑时,全家人齐心协力、喊着号子轮番上阵的架势,更是把过年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气氛烘托到了极致。
打糍粑,得先把精选的糯米浸泡一夜,久置的甑笼搬出来洗刷干净。第二天早早的,母亲就往大灶膛里架上柴火,烧得红旺旺的,把酥涨的糯米淘洗干净后,倒入垫了一张干净纱布的饭甑上,搬上大锅灶上隔水蒸。不一会儿,厨房里热腾腾的蒸气升起来,高高的烟囱炊烟飘荡,氤氲弥漫于青瓦老墙间袅袅婷婷,红旺旺的火苗映照着烟火里平凡的幸福。知道要打糍粑,家中的大人小孩都很兴奋,也不赖床了,也不吵闹着要出去放鞭炮了,都围拢到厨房来,你抢着烧火,我忙着搬柴,他忙着在灶里焖上几个红薯或者烘烤几个板栗鸡蛋。等待美味的过程,有开心守候又积极参与的兴奋。
趁着蒸糯米饭的间隙,我和姐姐一起把墙角的石臼挪出反复刷洗,木槌擦拭得干净锃亮。石臼在乡下称为“粑罐”,坚硬的花岗石凿挖而成,沿口粗内胆小,外饰波浪条纹。在乡下时,石臼不是每家每户都有,一般是全村共用一个置于祠堂,年节时分,各家各户排队轮流打糍粑,那场面热火朝天,年味十足,甚为热闹。
糯米饭蒸熟透后,掀开锅盖,浓浓的糯香扑面而来。冲糍粑是个力气活,又是个技术活,得趁热。母亲麻利地用盆把蒸熟的糯饭盛出倒进石臼里,打先锋第一个上阵的总是老当益壮的父亲。他用木槌快速地把糯米饭擂压成黏稠的团状,再举起木槌大力朝着糯饭团砸去,如此反反复复。一会儿,父亲已是浑身发热,满头大汗。一旁的二哥立马将他替换下来,糯米团越冲粘性越足,挑起来能拉好长,颇费力气。二哥喊着号子,围着石臼用力捶打,我们在一边给他加油数着拍子。一二十下后,二哥也是气喘吁吁,姐姐又接过木槌上阵。直至无米形,粘成粑,软糯劲道的糍粑就做好了。
第一臼糍粑往往是让大家尝鲜的。母亲清水净手后,从石臼里揪出糍粑放入大面盆。孩子们拿着筷子迫不及待地围过来,纷纷用筷子将糍粑一圈一圈挑裹成球状,在事先准备好的芝麻粉糖或黄豆粉糖碗里蘸一蘸裹一裹,放入嘴里软粘可口,又香又糯,韧劲十足,唇齿留香,美味极了!
接下来就是第二臼、第三臼,打糍粑“咚咚”的捶打声,吸引我们也想大展身手,跃跃欲试。13岁的外甥等了很久,急急接过木槌,模仿大人的模样打糍粑,拿起被糯米黏住的木槌,在石臼旁转来转去,满脸憋得通红,却怎么也扯不动,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我也不服气,抢过木槌也想尝试一下,深吸一口气,扎稳马步铆足劲拖起黏住的木槌,奋力向下捶,落下去时却软绵绵的,就像“哑炮”,根本捶打不出“咚咚咚”的效果。没一会儿,手也痛,腰也酸,上气不接下气,打糍粑原来这么难。母亲在一旁笑嘻嘻地说:“糍粑好吃事难做啊,任何劳动果实都来之不易呢。”
打好的糍粑会被揪到一个竹制的簸箕里,簸箕上面铺一层黄豆粉或刷一层油,这样,糍粑就不会粘在手上了。妈妈把那一大团糍粑捏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我和孩子们戴着上一次性手套,把糍粑放到模具里面。模具一般是圆形、梅花形或八角形,底部有动物、繁体字的图案,压平后模板上的图案就拓在了糍粑的上面。等糍粑冷却后,把取出来摆在簸箕上,模具上的图案固定后栩栩如生,非常好看。
记得原在乡下时,每逢村子里有人家订婚、嫁聚,女方父母打发姑娘回门礼,箩筐里挑回的要么是糍粑,要么是粽子。附近几个村庄每家每户都会送上几个沾喜气,俗称“散婚张”。那一个个白白胖胖的糍粑上面还会缀上一点喜庆的红,是凡俗里的幸福,象征着子孙延绵,亲邻和睦。
窗外寒风呼呼,室内打糍粑的现场热火朝天,舂臼声“咚咚咚——”铿锵有力。家里的男人们兴奋起来,越捣越快,伴随着“嘿哟嘿哟”的声声节奏。我们有的打、有的捏、有的印,分工合作,边闲聊着彼此的工作,笑谈着孩子们的趣事,妈妈乐得满脸的皱纹开成了一朵花。这热闹祥和的场景充满了团聚的喜悦,也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慰藉着一颗颗漂泊游子的心,我们把欢快和期许仿佛都揉进了这吉祥如意的糍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