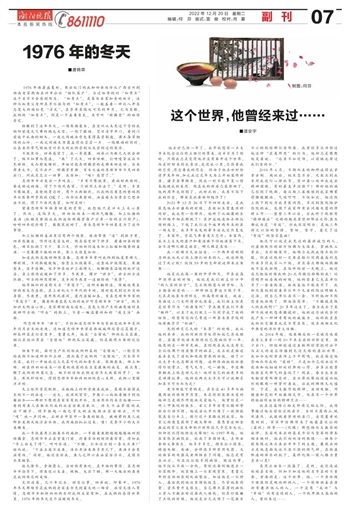■唐锦荣
1976年溽暑盛夏时,甫出校门的我和四弟结伴从广西宜州到湖南老家衡南县洲市公社“插队落户”。当过知青的对“知青点”这个名字不会感到陌生。“知青点”,是集体安置知青的地方,这种与知青父母所在单位挂勾的“知青点”,一般盖着一种比八开杂志宽大的桔红色“洋瓦”,在茅草屋随处可见的年月,尤为显眼。我俩的“知青点”,倒是一个盖着青瓦、名字叫“顺藕堂”的祖传老宅。
转眼到了这年冬天,一场寒潮袭来,在宜州从未见过下雪的我俩仰望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一饱了眼福。翌日清早开门,看到门前枝干虬曲的树木,一夜之间被冰雪包裹得晶莹剔透,灌木杂草相间的山岭,一夜之间被大雪覆盖得白茫茫一片。一饱眼福的同时,让在亚热带气候地宜州长大的我俩尝到从未尝到过的寒冷。
不胜寒冷,四弟感冒了,我一筹莫展。四弟以为熬几天就会好了,殊不知事与愿违,“熬”了几天,四弟咳嗽、打喷嚏等症状不见好转,反而愈发糟糕,开始还能在顺藕堂的走廊来回走动,后来浑身乏力,足不出户。顺藕堂东厢、百米之遥的忠顺爷爷不见四弟出门,问我是怎么一回事。我告知:“唉!感冒了。”
忠顺爷爷亦发出一声叹息:“乡里不像城里,看病好麻烦的,要走好远的路,得了个伤风感冒,只好用土办法了。”是呀,乡里不像城里,在爸妈身边时,有个头疼脑热,比我俩还着急的爸妈到单位医务所拿药就OK了,而今远离爸妈,油盐柴米全靠自己想办法不说,得了个伤风感冒,如何是好?
望着忠顺爷爷转身回屋的背影,我想他只是口头上关心罢了。然而,没隔多久,许奶奶端来一碗热气腾腾、加上红糖的姜汤(红糖是爸妈让我俩送给顺藕堂每户宗亲一份的宜州特产),吩咐四弟趁热喝了、散散寒就好了。原来忠顺爷爷回屋是为了这件事情。
加上红糖的姜汤里还有两个鸡蛋。连汤带蛋“送”到肚子里,四弟感激道,作用还是蛮大的,现在感觉好了许多。看看四弟的脸色,确实红润了不少。第二天,许奶奶仍送来加上红糖和鸡蛋的姜汤。一度萎靡不振的四弟,第三天恢复如初。
知道我俩没做好御寒准备,忠顺爷爷常叫我俩到他屋里烤火。那时候,乡间取暖做饭,除靠土灶烧柴草,还靠地炉烧煤炭。寒潮袭来,冻手冻脚,双手伸在地炉上面烤火、双脚踏在温暖的地炉边沿,身上很快就暖和了许多。冬夜里,围炉“讲古”,讲古的古道热肠,听古的神思缥缈,是乡间冬夜里一道独特的“夜景”。
稻草编织的座椅又名“草窝子”,这种坐躺舒适、保暖效果良好的原生态座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乡间,随时能见到它朴实的身影。冬夜里,屋外寒风凛冽,屋内温暖如春,坐在忠顺爷爷家的“草窝子”里,围着燃着蓝色火焰的地炉听忠顺爷爷“讲古”,既长知识又陶冶心性;老家那时尚未通电,蓝色火焰产生的幽亮映衬在凝神听古的“听众”的脸上,不啻一幅温馨祥和的“夜生活”画面。
听忠顺爷爷“讲古”,不但知道忠顺爷爷与家祖忠纯爷爷是同年同月出生的老庚,还知道忠顺爷爷曾在雁城城郊经营过菜园子,种瓜种菜是行家里手。耄耋之年,他在“自留地”种的瓜豆菜蔬,相比其他社员在“自留地”种的瓜豆菜蔬,仍是拔得头筹的佼佼者。
初来乍到,面对生产队划给我俩种菜的“自留地”,一脸茫然的我俩不知道种些什么好。因此属于我俩的“自留地”,只长草不长菜,我们一开始就过上无菜可吃的知青生活。寒潮袭来,难上加难。好在许奶奶送来一些夏秋收获的瓜豆菜蔬做的咸菜、酸豆角,解了我俩的燃眉之急。她不时还给我俩送些冬天收获的萝卜、白菜。寒风料峭时,得到忠顺爷爷和许奶奶的悉心关照,我俩心里暖洋洋的。
天上依然雪花飘飘,石板路上的积雪凝冻成冰,屋檐水凝固成长短不一的冰凌……这天,我顶风冒雪,步履小心地挑着桶子到池塘挑水——那时不像现在家家有机井水,生活用水均来自池塘——看到有鱼儿在取水形成的冰窟窿载浮载沉。许久不沾荤腥的我放下桶子,顺手捡起一块巴掌大的石块朝冰窟窿砸去,只听“噗”地一声闷响,正好击中其中一条鱼的脑壳。被砸晕的鱼儿旋即肚皮朝天地浮出水面,我用扁担扒拉过来:嚯!是条不小的大头鱼鳙鱼。
我一手扶着肩上挑着水的扁担,一手抠着鱼腮趔趔趄趄地回到顺藕堂。忠顺爷爷正在堂屋门前、捋着雪白的胡须看雪景,得知我“手上功夫了得”,呵呵乐道:“不错,打水还打到一条大头鱼!”继而说:“千滚豆腐万滚鱼,活水煮活鱼要多煮几下,鱼汤才会有滋有味。”同时,他还告诉我,鱼儿之所以在冰窟窿浮头,是因为水里缺氧。
数九隆冬,食物匮乏,这时候有鱼吃,是幸福的事情。在忠顺爷爷指导下,将鱼佐以生姜、辣椒、大蒜下锅,那一天做出的鱼肴是我俩难忘的美味。
光阴荏苒,几十年过去。回首往事,四弟说,印象中,1976年冬天那场雪是我俩到老家至今见到最大的一场雪。冰雪无情人有情,忠顺爷爷和许奶奶俩老对我俩关爱有加,在我俩的感情世界里,1976年的冬天是个温暖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