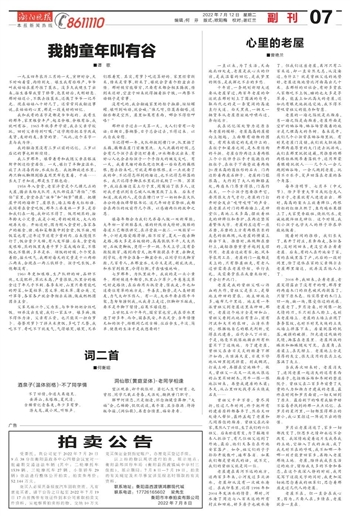■谭 歌
一九五四年农历三月的一天,寅卯时分,天不时响着雷,雨特别大。娘生我有些难产,爷爷叫我姑姑在屋外挂了蓑衣,没多久我便生了出来,接生婆帮我剪了脐带,包裹好后,天刚好亮。那时姑还小,不敢去挂蓑衣,还挨了爷爷一记耳光。现在姑姑八十好几了,还常常同我翻这事说,在姑姑的心里,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我和我哥的名字是都是爷爷起的。我哥生的那年,家里粮食丰产,起名余粮。余粮有谷,我就叫有谷。1965年秋季开学前,我去父亲学校玩,回时父亲特别叮嘱:“这学期你把名字改成友贤,友好的友,圣贤的贤。”从此,这个名字一直与我为伴。
我的脑海里没有三岁以前的记忆,三岁以后记的事也断断续续。
我三岁那年,娘带着哥和我随父亲在银溪附中侧边检堂居住。一天,娘打了半脚盆温水,放了点消毒药粉,水成红色。我把脚放进水里,两只脚从脚踝到膝盖用黑布包裹着,干痛……长大了才知道,那是生了脓包疮。
1958年入食堂,老家泮堂是个几横几正的大屋,腾出来给大队用。大队部设在“涛伯”、“根伯”家里,食堂办在“该爷”和“桐爹”横屋。把横屋中间的墙拆了,屋很长,墙上贴着大红标语。我同哥在食堂吃饭,那年三弟友林一岁多,是否和我们在一起,我却记不得了。饭用碗蒸的,按年龄大小定量,我是小碗,哥的碗稍大,大人的碗再大些。开始还好,因为刚入食堂时,各家各户的粮食、猪、鸡和菜都集中到食堂,饭不缺,咽饭菜也有,过年过节还有少量的肉。后来慢慢不行了,饭分量少又稀,有人发牢骚。后来,食堂越发艰难,蒸的饭里夹着干萝卜菜或鸡白菜,不像饭也不像粥,多半是水。领饭的时候,个个哭丧着脸,摇头叹气。我那时每天的定量是十六两称二两米,合现在一两三钱样子。孩子吃长饭,半饱都没有。
1960年更加艰难,生产队种的田,品种不纯,又没肥料,草比禾高,产量很低,队里分的粮食过了年几乎不剩。春季来时,山里只要有能吃的野菜,如夏枯草、菖义草、糯米草、蒲公英、艾叶草等,各家各户就会争相去采摘,做成粑粑团团当主食。
父辈兄妹六个,父为长,与爷爷奶奶分灶吃饭。四弟没出生前,我们一家五口。娘多病,做不得体力活,父亲有工资,也只能买一担白萝卜。每餐用萝卜丁拌点米煮饭,多吃了几餐,我吃不下。哥吃不下就发气,气得娘哭,娘哭,兄弟们跟着哭。其实,有萝卜吃还算好的。家里经常断米,借米是常事,断米了,娘就会拿着个脸盆出去借。那时候穷能帮穷,只要有米都会相互腾拨,借到米还好,空盆子回来就得捆着肚子饿,一两餐不动锅子是常事。
没有吃的,我会翻遍家里的柜子抽屉,坛坛罐罐。娘听到响动,就会喊:“徕几呀,你莫再翻嗒,还翻些都是空然,屋里如果有东西,哪会不得你呷咯?”
那种日子过去一天算一天,大人们常有一句话:日糊日,餐糊餐,日子总会过去,不得过来。以此自我安慰。
不记得哪一年,大队部搬到槽门口,队里插了丘藕,藕都在屋门前塘里洗。大人洗藕的时候,总会有几个孩子在旁边盯着看,口水都要流出来。有好心人也会丢给孩子一个手指大的嫩尖尖吃。有一天,我看见塘对面瓜兜边飘着一些白色的藕根根,想去捡来吃,可就是那些根根,差一点就要了我的命。不记得怎样到的塘边,也不记得怎样落的水,我只记得手脚在水里乱抖乱爬了一阵。冥冥中,我站在塘边菜土行子里,周围站了很多人,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被人从塘里救了上来。后来才知道,救我的人,是住在槽门口丁一奶奶和在大队办公的房叔谭帮银书记。这几年回老家祭祖,我都会在两位的坟前作几个揖,以感谢两位的救命之恩。
娘每年都会为我们兄弟每人做一双新布鞋,大年初一穿新鞋喜庆。娘的针线功夫特好,做鞋的每道工艺都很讲究,在泮堂数一数二。一双鞋穿一年,小时走路爱踢滑梯,鞋不经穿,夏天一般赤脚走路,路大多是石板铺的,高高低低不平,天太热时,石板烫脚板,烫得一步一跳。冬天上学,没有套鞋胶鞋穿,遇到雨雪天,把布鞋提在手里,赤脚走到学校。老师会准备一脚盆冷水,让同学们洗脚穿鞋,几百号人,共那盆水,又冷又是泥,胡乱洗洗,和水穿到鞋里,冷得打颤,牙齿嗑嗑地响。
七岁那年,为队里放牛,我放的是一头小黄牛。那时候连牛都苦,队里山少草少,牛崽崽没草吃时走路快,在后面用头抵背身,催我走,牛也知道要往有草的地方走。牛善良,勤劳,是人类好朋友,力气大却不伤人。有一次,大水牛要去跟牛斗架,急匆匆撞倒我,从我身上走过,但脚却不踩我,要不是牛脚下留情,后果不堪设想。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穷家也穷,我在苦水里泡了好多年。而今,国泰民安,丰衣足食。当年懵懂无知的孩子,转眼间已近古稀。往后余生,平淡、简单、健康的生活才是我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