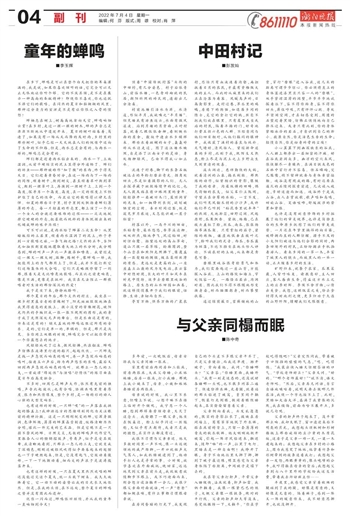■彭发灿
顶着“中国传统村落”头衔的中田村,有几分姿色。村子后依青山,前临水塘,一色青砖砌就的民居,朝阳斜照的砖瓦间,透射出几分沧桑。
村前池塘引活水为源,水清凌,形似半月,我欲唤之“半月塘”。但见塘底有游鱼逐云,水面有微风漾波。站到月塘的月背面,正对村落,就着几棵依依垂柳,看倒映水面的屋舍,縠纹中透出水乡模样来。那些衣着斑斓的女子,袅袅婷婷从水边走过,因了这汪塘水映照,自是添了江南女子的灵动。身处杨柳轻风,已由不得我心如止水。
流连于村巷,脚下的长条石板被远去的年轮打磨出青光。拐角处回头,尽是忙着摄影的人们。无人去探寻藏于斑驳墙缝中的记忆,也无人提及粘在檐口蛛网里的童年。轻轻推开一扇破旧木门,屋顶洞穿的光束,如一柄锋利长剑,欲划破陋室的尘封。吾亦时间过客,纵是窥见岁月痕迹,又怎能识破一屋子秘密?
村落以外,一马平川的田亩,水稻青青,渠水悠悠,香草溪边柳。双双新燕,贴地争飞,风过稻田,时时惊白鹭。抬望远处的高山草甸,漫山只披一层草绿,轮廓圆润,整个山峦在和煦阳光照拂下,像覆盖着一匹熨贴的绸缎,极具柔顺丝滑的质感。更远处是更高的山,一座座矗立山巅的风力发电站,在云雾中时隐时现,巨大的叶片如风车在时光中慢转。徒步去磨眼里峡谷的路上,原生态的山水田园如画卷,就这样慢慢展开于我们的眼前,恬静、生动、亲切而自然。
孕育万物、供养万物的广袤农村,恐怕只有血液连着沟壑,扁担挑着日月的农民,才最有资格做大地的主人。而此时从城里来的我们正在沦落为看客。风暖鸟声碎,日高禽影重。走村过巷,草丛里的鸡鸭,房檐下的狗猫,如退居乡间的隐士,觅它的食打它的盹,丝毫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只有屋里或坐或站的村民,隔着半掩的门,好奇地打量五颜六色的人群。不经意间与他们四目相对,从他们躲闪的眼神中,我收获了满村的善良与纯朴。天气晴好,清风怡人。曾经拼命逃离的乡村,此刻于我,既陌生又熟悉,脸上尽是与泥土之上乡野众生久别重逢的欣喜。
溪头涧边,慈祥勤快的大妈,就着清冽的山泉,捣衣刷鞋。那熟练的动作,似曾相识的背影,像极了我的母亲。沟渠纵横的田畴,偶见荷锄的农夫,似父辈伫立陇间,守望正在分孽的水稻,一言不发。我们听见风翻禾梢的沙沙声,或许他们早已听到“稻花香里说丰年”的热闹。天地渺茫,田野辽阔。风起原野,瓜果飘香。蜜桃、杨梅,已在枝头羞红了脸,丝瓜、南瓜,张张扬扬吊满瓜架。只有紫红的茄子,碧绿的辣椒,谦虚地低垂在枝叶之下,聆听我们的足音。西瓜、香瓜最为坦荡,不遮不挡坐在地头任人评论。不误农时的土地,从来都是秀色可餐。
磨眼里峡谷很考验勇气和体力,我们需要越过一座山背,方能探入谷底。上山的路陡如墙立,窄处仅容一足。一路怪石层出,沟洞时连。因此我们不得不跟随地形变换身姿,时而猫腰躬身,时而攀壁扶藤。
通过绿荫蔽日,苔藓铺地的山背,穿行“磨眼”进入谷底,这几米的距离可谓步步惊心。你必须将直立的身体塞进漆黑且只容一人的“磨眼”,双手紧撑湿滑的洞壁,半步半步地试探着往下,容不得你转身,容不得你回头,屏住呼吸,只有怦怦心跳。身处半密闭空间,才真切感受到,周遭的石壁趁着黑暗,仿佛正悄悄地向自己挤压过来。或者只有此刻,你的身体紧贴冰冷的岩石,才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敬畏自然,你是活色生香的生命;轻慢自然,你是粉身碎骨的尘埃!
小心翼翼下到幽深狭长的谷底,人人额上都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好在谷底岩洞众多,幽凉的空穴来风,很快驱尽一身燥热。在满目铁灰色的石林中穿行并不容易。怪石嶙峋,突兀桀骜,稍不留神就要与身体亲密接触。峡谷没有现成的路,有时还要在逼仄的石缝间探索前进。几次误入歧途,幸好迷途而知返。峡谷终于走成山谷,众人击掌放歌,歌声唱和鸟鸣,回旋山谷。笑语喧哗,舒缓跋涉的劳累和紧张。
也许是没有刻意修饰的乡村拓展了他们的审美视界,也许是简静直白的生命原乡抚慰了他们的审美疲劳。一片还在午梦里徜徉的向日葵,被蜂拥而至的人群惊醒。措手不及的小太阳们被迫与他们合影的同时,两条田埂外的村民,正纷纷掏出手机拍着游人。看来乡间的一草一木,丰富了城里人的镜头,而城里人的一举一动,正点缀着乡村的生活。
旷野归来,就餐于农家。瓜果菜蔬,人皆呼味美。请教奥妙,主人回应,客人唇齿生香,得益这方水土之上的应季时鲜。季候不舍万物,心情出美食。我想,这顿饭菜之美,除去食材得天时地利之便,更多归功于久违的山野阡陌,馈赠我们无限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