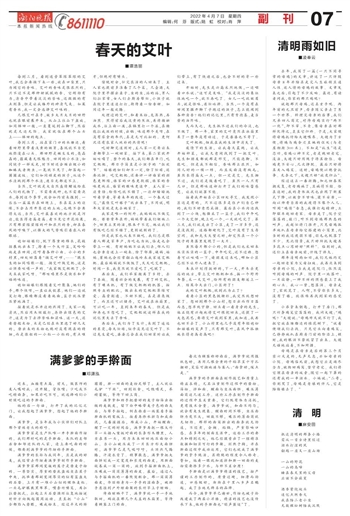■邓潇泓
近来,血糖有点高。前天,做医师的友人嘱咐我:迈开腿,管住嘴;少吃或不吃精面条,如果非吃不可,就选择咱们小时候吃过的手擀面。
他的后一句话,打开了我的记忆之门,让我想起了满爹爹,想起了他的手擀面。
满爹爹,是当年我与小伙伴们对队上那个曾姓老头的称呼。
满爹爹家是生产队唯一开手擀面作坊的。我们那时吃的是手擀面。本队的左邻右舍和邻近队的人家,逢上要吃面的时候,都要到满爹爹的作坊称手擀面。
满爹爹的长孙与我同年,且是我的好友,我经常去作坊看满爹爹制作手擀面。
满爹爹家那间宽敞的屋子是磨麦子粉的。一尊坚实、厚重的磨底盘端坐在屋子中央,托举着那副宽阔厚实的似有篮盘大的石磨。上片有一堆小山似的裸体麦粒。一头毛驴眼戴黑布罩,嘴套竹嚼笼,肩扛拉磨把式,拉起上片石磨循环往复地按逆时针方向做起圆周运动,直至把“小山”全都陷入磨眼,碾成粉末。经过半天的转圈圈,擀一回面的麦粉足够了,主人就让毛驴“下班”,回到栏舍,吃饱喝足,养精蓄锐,等待下回上岗。
满爹爹和助手把磨好的麦子粉筛出粗糙的麦麸皮,留下白中略带麦子色的面灰后,与帮手抬起,倒在面房一端装着手摇擀面机的案板上。接着再掺水拌匀和成面泥,几番揉搓后,堆成小山,开始醒面。醒了一定的时间后,满爹爹再把一根大竹竿一头插入案板对面的长条形木槽里,人坐在另一头,用力来来回回地压面粉小山。当小山被压成了一片长方形大面饼时,满爹爹已是气喘吁吁,头顶热气腾腾,汗浸衣背了。稍事歇息,满爹爹把大面饼划成一定宽度和长度的面皮,用擀面杖卷成一筒一筒的,放到手摇擀面机上,压碾成一筒筒薄薄的面皮。最后,通过人与手摇面机的一番默契配合,那一筒筒薄面皮,华丽转身为一手手的湿面条,被助手悬挂到户外晾面架的长竹竿上子晾晒。
待面晾晒干了,满爹爹就一手一手地取回,码放在那几个无盖的木箱里,等待着顾客上门称面。
毎次为顾客称好面后,满爹爹就用报纸包好,再用几根金黄的干稻草呈十字扎捆好,笑容可掬地递与客人:“面拿好,缓点走。”
满爹爹的手擀面在制作技艺和质量上精益求精,尤其注重制作过程中的磨粉、筛粉、拌和面、醒面与坐压面饼、碾压薄面筒这几道工序。这些工序在制作手擀面的过程中至关重要,它们既有体力消耗,更有技术含量。满爹爹说,和面不均匀,就会有夹生现象。醒面时间不够,坐压面饼力度不大,回数不够,碾压的薄面筒就无韧劲。那样的面筒擀出的面条就无劲道,不经煮,会糊、粘锅,严重影响口感。在多年的制面生涯中,这些工序的要点和精到之处,他已经摸索出了一组精准数据和切实可行的步骤,烂熟于胸,并在擀面过程中成功运用,它们也就成了满爹爹的拿手绝活,其精绝的程度令人称奇。譬如,他看一眼就知道拌和擀一回面的麦粉需要掺多少水,与秤不差分厘!
手擀面是以满爹爹精湛的技艺,按严谨的工序制作的,质量过硬,细滑而劲道,口感极好,渐渐在十里八乡声名鹊起,成了当地无牌名的品牌。
而今,满爹爹早已谢世,作坊也被子孙改建成了两层小洋楼,精湛的技艺也没传承下来,他的手擀面也“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