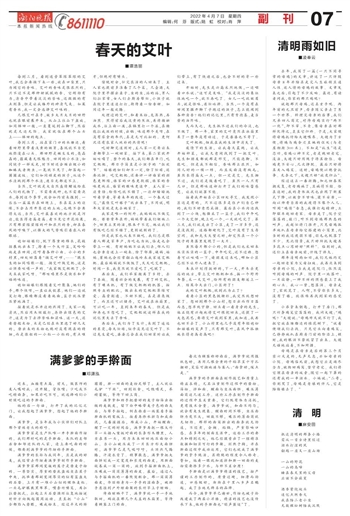■谭浩丽
每到三月,看到道旁翠绿翠绿的艾叶,我总会要摘下来一些,放在口袋里,只为闻它的香味。艾叶的香味是很浓烈的,只不过不是那种甜腻腻的香,它刚劲有力,清香中带着淡淡的苦味,还微微的有点刺鼻,但是让我格外的神清气爽。如果有香水,我一定会选择艾叶味的。
几根艾叶在手,故乡大片大片的田野也就在眼前展开来,从山上往山下盘旋,如同梯田一般,一直蔓延到山脚下,然后就是无边无际。我家就住在那个山头上——梯田的起点。
每到三月,站在家门口的水塘边,看着田野里带着浅黄的嫩芽,喜悦就不自觉地弥漫在心头。那田野是嫩生生的,亮晶晶的,蕴藏着无限魅力。田间的小水洼,如同镜子一样反光,时不时还会蹦出极小的蜘蛛或者爬虫,一晃就不见了,却荡起一圈圈波纹。它们如同顽皮的孩子,从这个水洼跳到那个水洼,连目光都追不上。
当然,艾叶就是大自然盛情赠送给农人们的礼物了。不需要栽种,也不需要浇水,每到这个季节,就会如约前来报到。一丛丛一簇簇长在田埂上,长在菜土的边缘,不会占用开垦过的土地,也绝不会离得太远,当然,艾叶最喜欢的地方就是河边,能长得老高老高。看不见它开花结果,只有那碧绿碧绿的叶和浓烈的香,却在春风的呼唤下,以强大的气势吸引着农人的眼球。
媳妇姑娘们,脱下厚重的棉衣,花枝招展地出来了,挎着一个大竹篮,笑吟吟地走在田间,还哼着各种小曲。小小的乡村里,四处回荡着“摘艾叶啰,……”脆生生的如同唱歌一般。摘艾叶做艾粑,这是必须要吆喝一声的。“我家做艾粑粑了,今天来我家吃呀。”那吆喝里尽是快乐和幸福的味道。
媳妇姑娘们跟随着艾叶聚集,她们的手,那个快呀,一直让我钦慕。她们一边说笑打趣,眼睛都没看着地面,篮子就压紧压紧地满了。
接着就是水井边的热闹了。大家一起清洗,然后用木槌敲打,再挤出绿色的艾汁,这是为了去掉苦味和涩味。这一天,还要磨糯米粉。米是已经在水里泡了好几天的,磨出来的米粉也绝对没有现在的精细,而是很粗的一小粒一小粒的,有点咂牙,但绝对有嚼头。
傍晚时分,忙完农活的人回来了。主人家也提前多准备了几个菜,几壶酒,大院子里早摆出桌子,坐的坐,站的站,男人们拉家常,女人们去厨房帮忙,小孩子就在院子里追追打打,期待着一份香甜。如同过年一般欢腾。
处理过的艾叶,和着米粉,先蒸熟,再油煎。煎得前后成淡黄的焦状,再将糖融成水,往上面一泼,在锅里打一个滚,在糖能拉成丝的时候,出锅。味道那个美呀,在没有零食的年代,真是无可比拟的。更何况还有农家人纯朴的热情呢!
吃好聊完道别时,主人家一定要让来者都带上一碗回家。接下来,第二家就开始吆喝了。整个的春天,我们都在串门,吃艾粑粑,那日子简直是小孩子的“狂欢节”。姑娘媳妇们却不一定,除了忙碌,还要比拼。吃艾粑粑,还要评一评谁家的颜色更鲜绿,谁家的口感更软糯,谁家的香味更纯正,谁家的糠味更适中。主人家一边责怪:给你吃就不错了,一边却暗暗地听着学着,等着来年的改进。一个春天过完,“最佳艾叶娘子”就出来了,不用说,明年大家就是先去她家了。
我家是唯一的例外。我妈妈从不做艾粑。爸爸常年在外,妈妈带着我们姐妹三个,田里土里的活,根本干不完。她让我们有饭吃已经不错了,更别说别的了。
但是我家也从来不缺吃。我们总是跟着人群走家串户,为吃也为玩,临走也会带上一碗。有时妈妈不让我们去,邻人们也会亲自送上一碗来。除了邻居,姨妈、姑妈、舅妈也会经常翻山越岭来我家送艾粑粑。最后妈妈就不做饭了,天天吃艾粑粑,时间一长,我竟然就不爱吃了,吃腻了。
再后来,我们举家搬离了乡村,去了县城。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了碎艾机,有了碾米机,有了做艾粑粑的机器,按照专业的配比,做出来的艾粑粑翠绿可爱、晶莹剔透、不甜不腻,真是漂亮极了。而且还可以储存,艾叶放在冰箱里,可以吃一年,直到来年的春天。但是我却再也不想吃了,艾粑粑就这样在我的记忆里失去了香味。
再后来,我们为了生计,来到了遥远的东莞,每天忙碌,似乎没见过艾叶了。不过先生爱吃,婆婆总会在我们回家时让我们带上,有了快递之后,也会不时的寄一些过来。
开始时,先生是兴高采烈地做,一边咽着口水说:“这可是美味。”我是淡淡的象征性地吃一个,就不再吃了。女儿一吃就皱眉头,说是怪味,连忙吐掉。当然,一个没有在田间里撒开脚丫子跑过的孩子,怎么能闻到各种清香?他们的记忆里,只有肯德基、麦当劳的油炸味。
久而久之,先生抵不过我们的冷淡,也不做了。那一年,家里的艾叶竟然在冰箱里呆了一整年没有动过。于是婆婆也不寄了。
艾叶粑粑,彻底在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疫情下的生活,让我每天晨跑,让我开始种菜,让我无意间找到了一把艾叶。先生和朋友都说那是祁艾,只能泡脚,不能吃。但是我不相信,香味那么浓烈,如同儿时的一模一样,而且反面没有绒毛,虽然长得高大一点,但一定是艾。先生拗不过,我们还是做着吃了。虽然一人只有几口,但是那味道却打开了我们的味蕾感觉,让我们欲罢不能。
接着我开始在小区四处寻艾。我发现小区还是有的,只不过很多是住户们自己种的,我们不好意思采摘。最后在小水沟边找到了一小块,勉强采了一篮子,我们中午吃一个大艾饼,晚上吃一个,一天就吃完了。第三天,我们就走出了小区,走了一万多步,还是没找到。道路都硬化了,艾叶没有了生存空间。我和先生失望之时,却突然在一个小院子的角落里发现了一大片。
虽然每片都小小的,但是我们也采回来压实压实的一篮子。中午吃完,还不过瘾。想着可以吆喝一下,请朋友过来吃,哪知小区已经不让外人进来了。
本来计划得挺好的,下一天,开车去更远的地方,带上艾叶粑粑和水,搞一个野外午餐,采一天艾叶,给所有的朋友都送上一点。结果今天出门,小区封了!
我的艾叶粑粑,就到此为止了?
看着小区的黑色铁栅栏,我突然就想回家了。想回到那个小山村,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想单纯宁静。回头看一看身旁的先生,他正饶有兴趣地将艾叶根挖回来,还提了一大包泥巴,要将艾叶栽到家里,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小山村里也几乎没有年轻媳妇和姑娘的笑声了,只有那艾叶,在风中孤独地长得老高老高吧?